|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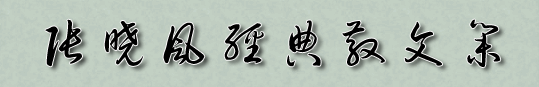 |
|
|
种种有情
|
|
 |
|
有时候,我到水饺店去,饺子端上来的时候,我总是怔怔地望着那一个个透明饱满的形体,北方人叫它“冒气的元宝”,其实它比冷硬的元宝好多了,饺子自身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张薄茧,包覆着简单而又丰盈的美味。
我特别喜欢看的是捏合饺子边皮留下的指纹,世界如此冷漠,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化为炭劫,但无论如何,当我坐在桌前上面摆着的某个人亲手捏合的饺子,热雾腾腾中,指纹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吃饺子简直可以因而神圣起来。
“手泽”为什么一定要拿来形容书法呢?一切完美的留痕,甚至饺皮上的指纹不都是美丽的手泽吗?我忽然感到万物的有情。
巷口一家饺子馆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东饺子馆,也许是一个四川人和一个山东人合开的,我喜欢那招牌,觉得简直可以画上清明上河图,那上面还有电话号码,前面注着TEL,算是有了三个英文字母,至于号码本身,写的当然是阿拉伯文,一个小招牌,能涵容了四川、山东、中文、阿拉伯(数)字、英文,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爱。
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例有的习惯,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劈头栽下一片叶子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
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过的车顶上,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我把叶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我札开微绿的指尖,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碧绿而芬芳,温暖而多血,镂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一叶在左,一叶在右,我是庄严地合着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们到堪萨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标准的神仙眷属,博士的先生,硕士的妻子,数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的年薪,高尚住宅区里的房子,房子前的草坪,草坪外的绿树,绿树外的蓝天……
临行,打算合照一张,我四下列览,无心地说:“啊,就在你们这棵柳树下面照好不好?”
“我们的柳树。”朱忽然回过头来,正色地说:什么叫我们的柳树?我们反正是随时可以走的!我随时可以让它不是‘我们的柳树’。“
一年以后,他和全家都回来了,不知堪萨斯城的那棵树的如今属于谁——但朱属于这块土地,他的门前不再有柳树了,他只能把自己栽成这块土地上的一片绿意。
春天,中山北路的红砖道上有人手拿着用粗绒线做的长腿怪鸟的兜卖,几吹着鸟的瘦胫,飘飘然好像真会走路的样子。
有些外国人忍不住停下来买一只。
忽然,有个中国女人停了下来,她不顶年轻,大概三十左右,一看就知是由于精明干练日子过得很忙碌的女人。
“这东西很好,”她抓住小投,“一定要外销,一定赚钱,你到××路××巷×号二楼上去,一进门有个×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弄外销!”
然后她又回头重复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开。
台湾怎能不富,连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指点别人怎么做外销,其实,那种东西厂商也许早就做外销了,但那女人的热心,真是可爱得紧。
暑假里到中部乡下去,弯入一个叉道,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看到一个身架特别小的孩子,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结着简单的结,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网花盆的吊篮。
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一边照顾着杂货店,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蝉声满树,我停焉为褡讪着和那妇人说话,问她卖不卖,她告诉我不能卖,因为厂方签好契约是要外销的,带路的当地朋友说他们全是不露声色的财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国逛梅西公司,问柜台小姐那架录音机是不是台湾做的,她回了一句:“当然,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台湾来的。”
我一直怀念那条乡下无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对富足的母子,以及他们怎样在满地绿荫里相对坐编那织满了蝉声的吊篮。
我习惯请一位姓赖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顾。有一年我打电话找他们,居然不在,因为到关岛去做工程了。
过了一年才回来。
“你们也是要三年出师吧。”有一次我没话找话跟他们闲聊。
“不用,现在二年就行。”
“怎么短了?”
“当然,现代人比较聪明!”
听他说得一本正经,顿时对人类前途都觉得乐观起来,现代的学徒不用生炉子,不用倒马桶,不用替老板狼抱孩子,当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口咬定现代人比较聪明时脸上那份尊严的笑容。学校下面是一所大医院,黄昏的时候,病人出来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两两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径上便遇见了几个这样的人。
习惯上,我喜欢走慢些去偷听别人说话。
其中有一个人,抱怨钱不经用,抱怨着抱怨着,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样,话题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块钱能买几百个鸡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个人憋不住地叫了起来:“你知道吗,抗战前,我念初中,有一次在街上捡到一张钱,哎呀,后来我等了一个礼拜天,拿着那张钱进城去,又吃了馆子,又吃了冰淇淋,又买了球鞋,又买了字典,又看了电影,哎呀,钱居然还没有花完呐…”
山径渐高,黄昏渐冷。
我驻下脚,看他们渐渐走远,不知为什么,心中涌满对黄昏时分霜鬓的陌生客的关爱,四十年前的一个小男孩,曾被突来的好运弄得多么愉快,四十年后山径上薄凉的黄昏,他仍然不能忘记…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那人只是一个小男孩,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钱的人,让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传奇故事…
无论如何,能去细味另一个人的惆怅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气异样的好,不是风和日丽的那种好,是清朗见底毫无渣滓的一种澄澈,我坐在计程车上赶赴一个会,路遇红灯时,车龙全停了下来,我无聊地探头窗外,只见两个年轻人骑着机车,其中一个说了几句话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啊!”我不知他们想出了什么好主意,但看他们阳光下无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不知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红灯前遇见一个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见到的人真是一个奇异的机缘。他们的脸我是记不住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他们石破天惊的欢呼,他们或许去郊游,或许去野餐,或许去访问一个美丽的笑面如花的女孩,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喜悦,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得到了,我惊喜于我能分享一个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悦。
有一次,路过香港,有事要和乔宏的太太联络,习惯上我喜欢凌晨或午夜打电话——因为那时候忙绿的人才可能在家。
“你是早起的还是晚睡的?”
她愣了一下。
“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孩子要上学,所以要早起,丈夫要拍戏,所以晚睡——随你多早多晚打来都行。”
这次轮到我愣了,她真厉害,可是厉害的不止她一个人。其实,所有为人妻为人母的大概都有这份本事——只是她们看起来又那样平凡,平凡得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么大的本领。
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她可以没有籍贯、没有职业,甚至没有名字地跟着丈夫活着,她什么都给了人,她年老的时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但她却活得那么有劲头,她可以早起可以晚睡,可以吃得极少可以永无休假地做下去。她一辈子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还是在拥有。
资深方妇真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敬的角色。
文艺会谈结束的那天中午,我因为要赶回宿舍找东西,午餐会迟到了三分钟,慌慌张排地钻迸餐厅,席次都坐好了,大家已经开始吃了,忽然有人招呼我过去坐,那里刚好空着一个座位,我不加考虑地就走过去了。
等走到面前,我才呆了,那是谢东闵主席右首的位子,刚才显然是由于大家谦虚而变成了空位,此刻却变成了我这个冒失鬼的位子,我浑身不自在起来,跟“大官”一起总是件令人手足无措的事。
忽然,谢主席转过头来向我道歉:“我该给你挟菜的,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真对不起,不能替你服务了,你自己要多吃点。”
我一时傻眼望着他,以及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那只伤痕犹在的手忽然美丽起来,炸得掉的是手指,炸不掉的是一个人的风格和气度,我拼命忍住眼泪,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个“大官”旁边,而是一个温煦的“人”的旁边。
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
那些粉笔字不知道铁路局允许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们不是宣纸上的书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笺上的墨痕,它们注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们存在的时候,它是多好的一根丝涤,就那样绾住了人间种种的牵牵绊绊。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来:缎:久候未遇,已返,请来龙泉见。
春花:等你不见,我走了(我二点再来)。荣。
展:我与姨妈往内埔姐家,晚上九时不来等你。
每次看到那样的字总觉得好,觉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爱,一份人间的必要的温度。
还有一个人,也不署名,也没称谓,只扎手扎脚地写了“吾走矣”三个大字,板黑字白,气势好像要突破挂板飞去的样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还是写给过往来客的一句诗偈,总之,令人看得心头一震!
《红楼梦》里麻鞋鹑衣的痕道人可以一路唱着“好了歌”,告诉世人万般“好”都是因为“了断”尘缘,但为什么要了断呢?每次我望着大小驿站中的留言牌,总觉万般的好都是因为不了不断、不能割舍而来的。
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人生也无非是种种羁心绊意的事和情,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