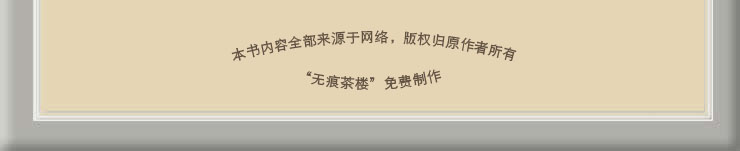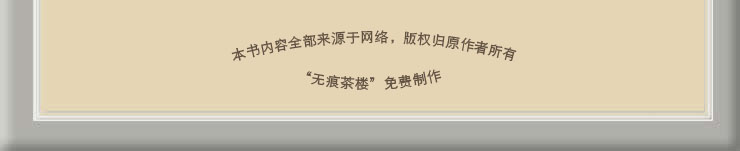|
附录: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
|
|
林舟(以下简称“林”):关于你的小说,人们常有一个话题是、你和余华、格非等在当代中国小说的语言的自觉,文体的自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你的小说语言独有的质地和色彩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就你而言,你对语言的自觉意识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有什么契机吗?
苏童(以下简称“苏”):意识到语言在小说中的价值,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左右或者更早一些,那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就是感觉到小说的叙述,一个故事,一种想法,找到了一种语言方式后可以使它更加酣畅淋漓,出奇制胜。从我的创作上讲这种对语言的自觉开始于《桑园留念》这样的以少年人眼光看世界的小说。当时也是努力从别的地方化过来为我所用;对我在语言上自觉帮助很大的是塞林格,我在语言上很着迷的一个作家就是他,他的《麦田的守望者》和《九故事》中的那种语言方式对我有一种触动,真正的触动、我接触以后,在小说的语言上就非常自然地向他靠拢,当然尽量避免模仿的痕迹。塞林格对我的《桑园留念》那一路小说的帮助和影响最大,我努力从他那儿学到了一种叙述方法。好多人认为他是个三流或者二流作家,但我非常喜欢,现在仍然对他情有独钟。
林:那么其他作家,我是指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家,对你的影响如何?苏: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我也很喜欢,从文学成就上说、塞林格可能不能跟这些大师们比,但像福克纳的语言你很难从他那儿学到什么。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他从大师身上学到的不太一样。
像备受推崇的麦尔维尔的《自鲸》,写作者如何学到它的精髓,从中获得直接的帮助,就很难说。
林:这里有一个接受者自身的问题,一个接受者所受的影响和启发不是以公众认可的大师的标准或其平均数为依据的。
苏:对,重要的是心灵的契台,塞林格唤醒了我,而可能对别人不起作用。好多写作者他所喜欢的作家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很怪,有人喜欢大仲马,有人喜欢格林,还有人喜欢茨威格……除了一些真正令人折服的作家,我想每个写作者大概都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像我的塞林格那样对自己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很大帮助的作家。
林:像《桑园留念》、《伤心的舞蹈》、《杂货店的女孩》等等这批小说,”少年眼光”就其实质来讲,是成年的你为小说的叙述找到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带来了形式感?苏: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小说写来写去,事件是不变量的,固定的,但一到每一个个体的反映形态上就千奇百怪,富于变化,因为有了特定的角度,属于你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的把握事件的方式。
林:《井中男孩》似乎是在放弃和打破这个“少年眼光”。
苏:当时的心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是形式意识觉醒之后变本加厉地讲究形式,如果不能创造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那就怎么也不会去定的。《并中男孩》就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它是不成功的,很生硬。到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还是有点做作,接着看《罂粟之家》就达到了自然松弛的状态,比较令人满意,现在回头去看,毛病也不多,就不错了。
林:你刚才说的“变本加厉地讲究形式”的心态后来在《妻妻成群》出现时就有了改变,是出于什么考虑?苏:当时我感觉到,再个性、再自我,写到一定的份上写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慢慢地耗尽。有了这样的意识之后,脚步就会往后退,在形式的要求上出现摇摆性。
写《妻妄成群》就往传统的方面退了好几步,想着看能不能写出别的东西来,也就是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结果发现我还能写别的东西,或者说还能用别的语官方式叙述故事。一九八八年时我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模糊的想法,感觉到这将是对自己一个挑战。以传统的方式,以人物关系和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的小说,《妻奏成群》之前我还没有过。
林:在《妻妻成群》、《妇女生活》、《红粉》这类小说之后或几乎同时,你开始了几个长篇的创作:《米》、《我的帝王生涯》、《紫檀木球》以及最近的《城北地带》。据说《我的帝王生涯》是你的得意之作,是吗?苏:我喜欢《我的帝王生涯》,是因为在创作它的时候,我的想象力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天马行空般无所凭依,据此我创造了一个古代帝王的生活世界,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已经有过的王朝,却又在一些根本方面似曾相识。
林:读你的《城北地带》,感到其中的氛围、一些细节、一些人物的特征,似乎都有很多是对你的《香椿树街少年》的短篇系列的复现,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呢?苏:我一直未能割舍我的那些“街头少年”小说,觉得在写了那么多短篇以后,应该写一个长一点的东西,把它们串起来,集中地予以表现,所以就写了《城北地带》,当然也就免不了你所说的那些方面的“复现’。但是我觉得很过瘾,觉得是圆了一个梦,并且也可能算是对我的“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
林:那么《紫檀木球》呢,这个“奉命而作”关于武则天的长篇,你有何感受?苏:这个长篇写得很臭,我不愿意谈它。我的小说从根本上排斥一种历史小说的写法,而《武则天》拾恰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种创作状态是多么不一样,而且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虚构,武则天这么个人物不好去虚构她的。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命题作文不能作,作不好。
林:最近我谈到你的两个短篇,一个是《把你的脚捆起来》,它让我想起你前几年的一个短篇《一个朋友在路上》;另一个是《那种人》,觉得它在你的小说中显得有些特别,夸张、荒诞的成分突出,好像偏重内心情绪经验的表现。
苏:有时候写小说可以不动情的,像舞台导演一样,让故事在叙述中非常戏剧化的表演。但《把你的脚捆起来》和《一个朋友在路上》,跟我的生活现实关系比较紧密,调动了我的身心体验。《那种人》这样的小说你觉得特别,是因为我写得比较少,在这篇小说里我强调厂个人感受,而把细致微妙的写实成分省去,通过夸张表现个人与世界的隔阂。小说写作的乐趣也就在这里,很难想象一个人老是在写同一个大循环,变来变去最终还是我苏童的东西。有的朋友认为我是用几把刷子在写,三把甚至四把,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怕风格的连贯性的失去。
林:你的创作不断从已有的叙事范型中努力跳出来,寻找着更为切合你的当下状态的小说方式,这给你的创作带来了活力。那么现在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的小说叙事观念上的变化使你感受深切的有哪几点呢,能否总结一二?苏:一九八二、一九人三年我也在写,那时是纯技术模仿。《桑园留念》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创造小男孩的世界。当你抛掉了别人怎么写的压力,自己在那儿很过瘾地说自己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了自己的创造力,这非常重要。到了《妻妻成群》,我又发现有时可以不必强调自己个人的创造,而去沿袭和改造古典的东西。《妻妻成群》,可以说从叙述方法到故事形态到人物关系没有一样是新的,但人们愿意看。它的好处在于自己能够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而不必要永远在自己身上“打洞”,可以“拿来主义”,可以对旧东西重新发现。当然这样的东西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多写,但这些过去年代的女性的故事。我一旦发现它还能写出来就还照写不误,并不顾忌有人觉得苏童的风格模式不变。
同样我个人不会痛恨自己曾经有过的任何所谓风格的重复,正如你所感觉到的、《把你的脚捆起来》跟几年前写的《一个朋友在路上》有精神的联系。有时会回去的,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永远往前走,一个人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极限,想象的空间在缩小。我觉得30岁以后的想象力无可挽留地衰退了,我现在很难保证我能否写出《我的帝王生涯》那样的作品来。
林:考虑到想象力的衰退,在你今后的创作中将以什么去替代它来支撑你的小说空间?苏:现在可能转向对所谓个人情感方面的表现,像《那种人》、《把你的脚捆起来》这样的作品,至少在这几年里可能在我的创作中会出现得多一些,我特更多地从个人生命内在体验的方面思考与对待小说。
林:这里我想起一个话题,就是有人将你的少年故事之类的小说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经验匮乏的补偿,对此你自己怎么看的呢?苏:可能在有些评论者的眼中没有一个作家的生活不会是匮乏的,而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匮乏的。一个关在牢里三十年不见天日的人,一个在社会上三十年不停奔走参加了各种重大的社会活动的人,这两人之间有一种不可比性。前者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三十年里沉思默想,也与这个世界、宇宙对话,他的生活不仅不匮乏、而且更厚重纯净,这恰拾是文学所倚重的。而另一种生活,它的社会信息量固然很大,但不一定对你的写作产生益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就此强调作家应该过前一种生活,而是想指出,对一个作家来讲不存在生活匮乏的问题,作家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创造活动,它遇到的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象力的匮乏、创造力的匮乏。
我们现在一些人考虑小说,仍有这么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是想将小说从艺术中分开。小说因为用语言说话,它必须记载社会事件、人际关系等等,这就引起歧义,实际上一个小说家跟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在内在精神联系上是一致的。一种新的音乐会被认为创造了对世界的沉思默想的新的形式,没有人指责它对社会不关注,而这样的指责却每每落到小说家头上。
林:从客观上讲,小说运用的语言,是许多东西共用的,像法律、通讯报道、政令文件等等。作为艺术的符号,它远没有色彩之于画家、音符之于音乐家那央纯净。
苏:是的。我是更愿意把小说放到艺术的范畴去观察的。那种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对它的拯救灵魂: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夸大,淹没和极曲了小说的美学功能。
小说并非没有这些功能和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小说原始的动机,不可能承受这么大、这么高的要求。小说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存方式,对我来说,我是通过小说把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就像音乐家通过音乐、政治家通过政治,其他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样。
林:在你的很多小说中都一再出现“逃亡”这个动作,它是你小说写作时的一个兴奋点吗?苏:你提的这一点蛮有意思。“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前些年的创作。入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台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我的一个短篇就叫《逃》,还有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小说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的东西来阐述、来展开的,小说必须从形象着手,说穿了就是从某一种动作着手,有时候就是一些动作,结果成了小说的出发点或背景。
林:在你的短篇小说结构上,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它的回环,有时是封闭的有时是半封闭的一个圆,这在《妻妻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等中长篇中,也很内在地支撑着你的小说。它们的这种形式感往往将人引向你的小说中的宿命意昧和循环论思想的把握。
苏:有时候好的主题与好的形式真是天衣无缝的。
这么一种人物的循环、结构的循环导致了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有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只是先有了形象上的回旋,写出来后我心满意足,发现了这种循环的思想意义。
林:也就是说小说的形式感将你引向了思想意味的求救。
苏:我说这种形式感与世界现有关系,恐怕不算玄吧。比如你发现有些作家他经常乱写,写着写着突然插进一段泥沙俱下的胡说八道,这跟他对世界的拒绝态度、对这个世界把握时的梦晓特征及批评这个世界的情绪状态是有关系的。形式的背后就站着那个怪人。我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看法确实有一种循环论色彩,从远处看,世界一茬接一茬、生命一茬接一茬、死亡一茬接一茬,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产生,你要说二十世纪的世界与十五世纪的世界,除了表面上的社会结构之类的东西不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个国家一群人在那里从事某种职业或事业谋生,在那里生老病死。
林:读你最近的短篇《那种人》,感到它的结尾也是暗示那种循环,只是它以悖反的形式出现而已。现在我又想谈谈你的少年故事了,我觉得《舒农或南方的故事》这一篇将你的少年故事中的一些东西推向了极致,我是指其中的舒农,作为一个少年在成人世界里的生活、受到种种的压抑以致畸形和变态,一种毁灭的激情异常灼人。
苏:对,不过我倒不认为是什么变态,而是一种对抗,在一种你所说的压抑的环境下,我要写出的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只是我将它按在了一个小孩的头上,而且他所对抗的对象,从他的家庭家族出发,可以引申到整个世界。
林:也就是说,他所承载的是此在的现实的某种感受和情绪。我觉得这一篇突出,还在于它与《桑园留念》、《杂货店的女孩》等相比,对美的留恋和流逝的表现相对淡化一些,而后者在丹玉、蕾这样的女孩的形象上给人强烈的印象。
苏:我的小说中普遍有这么一种情结,美是特别容易被摧毁的,本来就不多,很容易受伤害,或者说是变质。还有好多小说中我自己想是美的退化和伤害。这种东西从小孩的眼光看取,是最敏感的或者说是最清楚的。
林:又是不知不觉的。当你客观冷峻地写非常成人化的题材的时候,这种情绪或者说情结仍然存在,而且往往通过女性形象的创造而传达得更为浓例一些,像梅珊、颂莲、织云等,还是刘素子,她虽着墨不多,却因此给人很深的印象。
苏:我有这么一种愿望,刘素子还是应该在浴盘里洗澡的女孩子,而后来她给土匪枪到山上去了。这些说穿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美的幻灭是一贯的主题。从古典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所有美的东西都是易被摧毁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备受摧残与折磨,最后传达出悲观的宿命论。从中生发出某种对世界对人生的感悟,现代小说难以摆脱这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我的小说好多没有太强的现代意识;传统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背弃的。
林:你的小说对女性人物的表现,除了传达出美的幻灭、摧折和变质外,另一个很突出的情绪是孤独,这方面我觉得《樱桃》最具有代表性。
苏:孤独倒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当然传统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和认识不算太清晰。我相信这个命题虽然可以演变为许多细节,但作为一个大命题它是永恒的,就像爱情一样。《樱桃》写的就是孤独;其实前面谈到的《那种人》也是。《樱桃》的外壳很古典的,几乎就是一个人鬼恋的故事。这篇小说来源于一次聚会,一帮朋友在一起聊天,每人讲一个鬼故事,许多鬼故事很夸张很青面撩牙,却没让我心动,只有黄小韧说的一件事触动了我。他说是文革时,南大与鼓楼医院后面之间是一条小巷,没什么人家,一天黄昏,一个男人从这条小巷的一个门口定过,突然遇到另一个男人并被他抓住聊天,聊得非常好,他们大概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最后这个男人给他一块手绢,他也居然收下。并相约去找他,没两天这个男人真的去找他了,按照他留的地址找到了医院,一打听才知道,那个男人在太平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无人认领,于是这个男人走进了太平间,看到那具尸体,手里握着他送的那块手绢。我把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男人换成了女人,这就成了《樱桃》这篇小说。
林:将原故事中的男的改成了女的,大概使孤独在凄美的映照下愈显透亮了。女性,孤独,美的幻灭,这些让我想起有人在谈到你的小说时,指出你很受日本小说家:像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的影响,尤其是女性的描写方面,你能就此谈谈吗?苏:其实我并不太喜欢日本作家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可能宣泄得非常淋漓尽致,但软绵疲查,缺少张力,你比如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就给人醉入花丛的感觉,那背后隐藏的东西不能满足我。这方面给我启发很大的是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言二拍》,它们虽然有些模式化,但人物描写上那种语言的简洁细致,当你把它拿过来作一些转换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一种乐趣,你知道了如何用最少最简洁的语言挑出人物性格中深藏的东西。当然你对福克纳式的背后有一种博大的东西、一种对人类问题的关心,也得有感觉。
林:你的几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当你的小说以另一种形式传达以后,你对它的关注如何?苏:我很喜欢电影,所以跟导演有接触,完全出于对电影的喜欢。我的《妻妄成群》、《红粉》都是由我国著名的导演执导的,应该说都是还不错的。小说缀电影毕竟是两回事,冷静地想不应对电影有所奢求。镜头中竞难以捕捉到小说的语言能够产生的意味,无接完全传达小说的气息,相反,小说的表达没有镜头来得那么直接,给人的视觉印象那么强烈,小说给你那么大空间让你玩味、想象,当然也容易走失。
从小说到电影,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少有导演是真正喜爱这部小说才把它搬上银幕的,国外情况我不太清楚,就国内而言,导演往往是就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一组人物关系或情节,觉得这个可以拿来拍电影。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最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小说,只是这些小说的一些个碎片,而且是按照导演的方式串接的,所以中国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好多是成功的,那是导演的眼光,导演对这个小说的见解也能够成立,而与原作者的那种精神上的联系基本上是割断的。也有非常理想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结构,像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一个十几个小时的巨片《亚历山大广场》,就是根据德国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写柏林底层市民生活的长篇拍摄的。法斯宾德小时候看这个小说非常喜爱,到青年时看仍然喜爱,后来把它搬上银幕,以致什么都不舍得扔弃,一拍拍了十几个小时。导演与小说这么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令小说家欣慰,是最理想的,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
林:《妻妻成群》改编成电影后,你的名声大噪,被认为是“走红”的作家,你对“走红”怎么看?苏:这其实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就这么认为。
好像普遍有一种误解:书印得很多就变得流行和通俗了。我觉得我的小说除了个别的,我兴之所至地写的好多小说不可能为许多人喜欢;对此我自己没弦解释。我感到,电影及其他传播媒介会改变一个作家本身的面貌。像贾乎凹的《废都》出现,经舆论一“炒”,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仍然认为贾平凹是个非常好的作家,他的“商州”小说放在那儿,排除许多的嘈杂,仍然显示出很高的价值。《废都》那么一“炒”,竟然改变了他的成色,还有多少人认为他是个纯文学作家呢?《废都》一下子印了一百多万,贾平凹就成了一个通俗作家了。有多少人去关心作者本来的意趣呢?林:有一次我在山西路书摊上拿起你的《米》,老板说:“这书好呀,是苏童写的,苏童你知道吧?”我说我不知道,请你介绍一下。他说:“嘿,就是写电影《大红灯笼》的作家,很有名的。”我说好吧,我就买吧。
苏:书商就看什么好卖,《米》的写接其实跟流行通俗不沾边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关于“性”的描写,他们感兴趣,就成了受到书商欢迎的东西,慢慢的书商就觉得好卖,你的什么书他就都要了,书的发行量上去了,你就成了一个通俗作家了,谁去管你本来的意思?林:《米》的“逃亡——挣扎(奋斗)——回乡”三段式,在整体上就是一个象征。
苏:它负载的命题就是我设想的人类的种种团境,它们集中于王龙一人身上,这个人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人带着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种种问题发生关系,陷入困境。当然它比较主观,拆射世界的色彩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有阴暗、残酷,但这是人必须面对的东西。
林:大众文化对作家本来面目的歪曲和冲蚀,在当今中国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国外的情况就是你所知是怎样的,比如说美国吧。
苏:像诺曼·梅勒,他的《郐子手之歌》一出来即很畅销,但他并没有被当作通俗作家,他怎么写也不会是一个通俗流行的作家。
林:如果不从对你个人真实面目的了解出发,那么,现在你这种书的印数可观的状况对你的生计来说倒是不错的。
苏:只会对我有好处,只是我在一种误解中生活得很好,这很奇怪。
林: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你怎样看待你已有的名声呢?它对你构成负担吗?苏:古人说得好:“过眼烟云”,它对我不构成负担,构成什么负担呢?我当初写小说时从没指望我的书发行到六万册什么的。关于名声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比喻,有了名声就像是在路上捡了一个钱包,检到检不到都属正常,前者概率很小,检到自然高兴,但你不能检到钱包就不走路了,也不能永远检到钱包,你还得永远地走下去。
林:你对目前中国的文坛有何基本的估计?苏:有人认为这两年中国的文学滑坡了,我觉得好作家还是很多,比前几年多得多。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对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好事,它让你抛弃那种想一下子就出人头地或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全国人民都认识你的妄念,老老实实地去写,出现写作上的韧劲。以此维系小说家的存在和生命力,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篇作品确立自己,而要一大堆作品,你不能倚靠所谓社会命题,而必须呈现极具个人色彩的作品,靠个人小说自身的魅力、语言文字的奇迹来唤起认识和尊敬。在这样的局面下,不是为了写作之外的东西,而是真心地爱写作,希望得到的就是写作本身能够产生的东西的作家,有更加阔大的生存空间。
林:你对同行们的具体作品关注程度如何?
苏:前几年在《钟山》作编辑看得多,这两年少得多,真少、只读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像前不久我读到《收获》上余华的一个短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就非常喜欢、它可以说是我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非常的古典、朴素,又非常的深刻、意昧深长。
林:你、余华、格非等人近年的创作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入从中概括出“先锋性的失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苏:评论的语码跟创作的实际永远不是一回事、谁会想到我是要“先锋”才写作的?我只是想到我怎样写出满意的小说而写作的,所以也并不顾忌什么什么会不会失去。余华也很明显,你说他“先锋”勉强,说他“古典”也不古典,他并不顾忌现有的相对固定的界定和容易被套进去的某种理论。我想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能写,是继续写下去,大家都在认真地写着,在写作中遇到各自的问题,并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和招数去解决。
林:你对文学界的一些活动持什么态度?你近年的创作量似乎不是很大。
苏:对一些活动我能逃则逃。就我现在的状况而言,比较平静,感觉冲动多就多写一点,能够写作才是最重要的。我没把写作看得非常神圣,也不是被外部所说的那些命题占有着,比较单纯。一林:你已有的几个长篇都不算长,中篇不是很多,大量的是短篇;你还打算写长篇吗?苏:长篇可能还会写昭,但我更喜欢短篇,它往往写一个单纯的事件,或者由很单纯的念头引发出去,它可以一气呵成,精神情绪上不用负载太多。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使人在写的时候没有出现困顿、疲乏阶段时它就完成了,所以我一直比较喜欢短篇。
林:你刚才提到许多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并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招数去解决,你本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抛弃(肯定是要抛弃的)所有你从前已经驾轻就熟的小说路数之后,你如何找到新的方式方法,当你觉得想象力已经不如五六年前那么有一个神奇的翅膀而显得“匮乏”,创造力不如前几年,那么还有什么?这个东西我现在自己也还说不清楚,光说有经验不行、经验是比较脆弱的、也是比较虚假的。
我还在找另外一种写作方法,我并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长短优劣,“寻找”是永恒的。
(根据1995年6月20日下午谈话录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