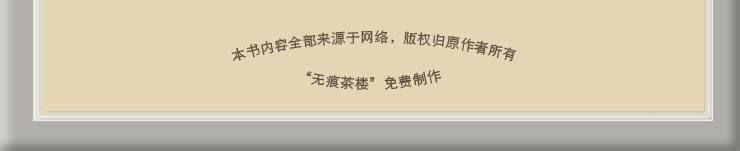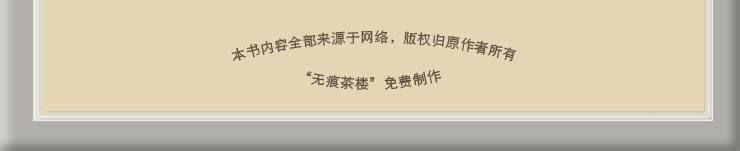|
星期六
|
|
这个叫老漆的人其实还很年轻,小孟夫妇知道他比他们年轻,但他们还是亲热地喊他老漆。这是习惯,所有的习惯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即使错了也不宜更改,你一旦要改口大家都觉得别扭,就像这次,宁竹突然问老漆,小漆,现在几点了?屋里的两个男人好像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们猛地回过头望着门边的宁竹,目光里含有程度不同的受惊的成份,他们的这种反应使宁竹显得特别尴尬。
我们家的挂钟坏了。宁竹嗫嚅着说,老漆,你不是带着手表吗?
老漆无声地笑了笑,他在自己的手腕上扫了一眼,九点钟了,我该走了,老漆站了起来,他的动作有点慌乱,膝盖撞到了茶几,胳膊差点把水杯带到地上,老漆手忙脚乱了一阵,把杯子交给小孟,他朝夫妇俩做了个鬼脸,他说,我该走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别急着走呀,再坐一会儿,宁竹的脸上有一种藏不住的愧疚之色,她挡着门说,你别误会,我们家的挂钟真的坏了,坏了半个月了,我让小孟去修,他就是拖着不肯去,你说他有多懒。
我该走了,九点多了,是该走了。老漆说,我明天也有事呢,我们单位最近很忙。
我们家现在没时间了,我那块手表忘在我姑妈家了,宁竹凭着一种惯性继续解释着,她说,小孟的手表从来就找不到,像他这么丢三拉四的人世上少见,买了多少块手表了,买一块丢一块!
老漆已经走到门边了,他突然转了个身,对小孟说,去,把你们家的挂钟拿给我。
什么?小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坏了吗?老漆说,我弟弟会修钟表,你们不用拿到店里去修,乱收修理费还不说,他们会把你的好零件换掉,这事交给我,一分钱也不用花,保你走上两年不会坏。
不用了,不用了,小孟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他说,哪能什么事都麻烦你?钟也不一定就坏了,说不定我买的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
别跟我客气,老漆说,去,把钟拿下来给我。
小孟看了看宁竹,宁竹却躲避着他的目光,她对着那面墙莫名地叹了口气。小孟就从她身边绕过去,搬了张椅子站上去,摘下了那只挂钟。
那天老漆是抱着一只挂钟离开小孟家的。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街上没有路灯,小孟夫妇在门外送客,只看见老漆的白色衬衫在黑暗中闪着影影绰绰的光,老漆大概把挂钟放进了自行车的铁丝篮里了,他们听见了挂钟在里面晃动的声音,老漆跨上了自行车,然后他们听见他在黑暗中说,星期六,星期六我再来。我把钟带来。``
世界上每天有多少火车在铁路上飞驰,每列火车上有多少人紧邻相坐而成了旅伴,但又有多少旅伴最后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呢?萍水相逢的人总是聚散匆匆,在火车到站的时候甚至来不及道别,下了火车后很可能在一个小时以后就忘了邻坐的模样。小孟从来没有预料到一次短短的三小时的旅程会带给他一个永远难忘的朋友,你怎么想得到呢,一个在火车上与你随意攀谈的人后来成了你的朋友。
老漆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小孟现在都记不清他们在火车上聊天的话题了,好像聊到了飞碟,聊到了股票,还聊到了爱滋病,他们聊得投机,就因为是海阔天空的聊,大家想把旅途上的时间用最自然的方式打发掉,三小时的时间确实很轻易地打发掉了。他们在月台上互相点头分手,小孟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让老漆停住了匆忙的脚步,大概是他的行李,他随身带着三件行李,两个旅行袋,一个纸箱,他把一个旅行袋背在肩上,左手和右手同时去抓取另一个旅行袋和纸箱,对于小孟来说,这点行李没有任何问题,他抓住了旅行袋,纸箱却被别人先提起来了。小孟看见火车上的邻座向他露出了友善的微笑,他说,我来帮你拿一个吧,你不是住车站新村吗,几步路就到了,我帮你拿回家。小孟谢绝了几次,最终还是半推半就了,因为老漆的目光那么透明而纯净,几乎带着某种期盼。小孟就这样犹犹豫豫地把老漆带回了家。小孟记得那天老漆没有进他家的门,他请老漆进屋喝口茶,老漆说,我不进去了,我还要去单位,我们单位最近很忙。小孟就说,那你方便的时候来玩吧。小孟当然是一句随口的客套话,但他记得老漆对他这句话很认真,老漆甩着手腕想了想说,星期六,星期六我来吧。
星期六后来就成了老漆来访的日子。
小孟夫妇都不是那种乐于广交朋友的人。老漆第一次来作客的那天夫妇俩有点不知所措,但良好的修养使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宁竹不认识老漆,她以为老漆是小孟在大学里的同学,就在一边感叹人情冷暖,说小孟的影集里那么多照片都是昔日同窗的,他们勾肩搭背满面春风的,看上去关系是多么亲热,如今却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只有老漆还记得来看看老同学。小孟不便纠正他妻子的错误,他只是嘿嘿一笑,是老漆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是大学生,我那年高考差一分,差一分上分数线,我天生倒霉,后来就没再考过。宁竹反应快,她话锋一转就开始批评大学生们的种种无能之处来了,她说,有什么用?我们家小孟是名牌大学的,可他连电灯都不会装呀,宁竹这么一说老漆便会意地笑起来,他点着头说,是呀,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认识的大学生都不会装电灯,会电工的都没上过大学,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宁竹说,那你肯定会电工活了,以后我们家的电工活就找你了?老漆说,没问题,随叫随到。
他们并没有在电的方面麻烦过老漆,他们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麻烦老漆的意图。但是老漆后来却帮了他们一个大忙。这是他们事先无法想象的,几年来小孟一直想从他工作的研究所跳槽去高新技术开发区,一直不能如愿,他随口与老漆谈过这件事,他真的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只是为越来越贫乏的聊天内容增加一个话题,可老漆却神秘地微笑起来,他说,你想去开发区?我们可以想办法的,只要你们研究所肯放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小孟说,他们招聘的时候我去过,他们好像对我很满意的,可最后却没了下文。老漆说,这不奇怪,你没有路子么,开发区工资高待遇好,大家都削尖脑袋往里钻,就比谁的路子大么。小孟不无轻蔑地说,是呀,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懒得去走这路子,他不稀罕我我还不稀罕他呢。老漆注视着小孟,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忍不住笑了。小孟说,你笑什么?老漆说,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这个毛病。小孟知道他指的毛病是什么意思,小孟没说话,然后他发现老漆的手啪地一声打在他的膝盖上,老漆说,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小孟觉得老漆的样子很神秘,但他没有追问什么,事实上关于开发区的事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想去开发区,但留在研究所也死不了人,小孟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那天他用一种调侃的口吻对老漆说,怎么啦,是不是你父亲在开发区当总指挥?
在开发区当领导的不是老漆的父亲,是老漆的一个亲戚,小孟很快就知道了,仅仅是在三天以后,小孟就得到了去开发区面试的机会,更让他受宠若惊的是那个领导把他送出办公楼的时候说,我们明天就发调令。小孟在电梯里急速下降,觉得自己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当他走出开发区大楼时一眼看见了老漆,老漆坐在花坛上向他挥手,小孟的梦就醒了,小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多少梦的成份,他问老漆,王副指挥是你什么人?老漆说,你问这干什么?小孟说,不干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老漆笑了笑,说,你们知识分子,什么事都好奇,好奇心能当饭吃吗?小孟一时有点发窘,老漆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老漆说,算是个亲戚吧,亲戚关系不算什么关系,主要还是算朋友吧,是一天天处出来的关系。
小孟夫妇知恩图报,小孟去开发区报到的前一天夫妇俩到商店里采购送给老漆的礼物,按照流行的送礼惯例,他们买了好烟好酒,宁竹毕竟心细,她说老漆总是胡子拉碴的,给他买一只电动剃须刀吧。小孟说要买就买高级的,结果他们就把一只一千多元的飞力浦剃须刀买下来了。正如夫妇俩所预料的,老漆不肯收那堆礼物,他说,早知道你们知识分子也这么俗气,我就不管你们的事了。好在宁竹伶牙俐齿,她说,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事情,你替我们跑路子一定花费了不少,你要是连这点东西都不肯收,那小孟就不去开发区报到了。话说到了这个地步,老漆才表示收下香烟和酒,而对于那只电动剃须刀的处置则充分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他说,剃须刀我也收下了,不过我不带回家,带回家我也是拿去送人,不如你们替我保管,反正我经常来,来了就能用,不一样是我的吗?
以后的日子里,小孟家里就经常响起电动剃须刀吱吱运转的声音,那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偶尔也会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天的傍晚。老漆的来访就这样成为小孟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老漆是在假日里来访,这样的日子里宁竹作为一个主妇尤其忙碌,她在做饭洗涮的时候总是能听见老漆在客厅里转动剃须刀的声音,住房太小了,宁竹在厨房里也能听清三个旋转刀头切割胡须的声音,老漆的胡子太硬了,隔着两个空间宁竹也能分辨出老漆的胡子被剃须刀吞咽的声音,有一天宁竹突然觉得很烦躁,她在厨房里脱口而出,吵死了,烦死了!
两个男的没有听见宁竹的埋怨,那天老漆告别的时候宁竹没有像以往一样送客,她闪进了卫生间。老漆走了她才出来,她的表情仍然残留着一丝厌烦之色。她对小孟说,你们在那儿聊了一晚上,聊什么呀?三天两头这么聊,聊什么呀?哪儿有这么多可聊的?小孟注意到了妻子的情绪,他说,我也不知道聊的什么,他坐在那里要聊我就陪他聊么,有话就说,没话就喝口茶,喝口茶就又想出话题来了。宁竹皱着眉,她说,奇怪,他老是说他忙,那么忙为什么这样呢,什么事也没有、在你家一坐就是一晚上,一下午。小孟说,你烦他了?他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帮过我们大忙呀。宁竹说,我知道我不该烦他,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听见那剃须刀的声音就烦了,就像是一群蚊子在我耳朵眼里嗡嗡的飞。早知道这样,我那天应该逼着他把那剃须刀带回家。
他们欠了他很多了。除了父母,除了兄弟姐妹,还有谁比老漆对他们的事情更热心呢?小孟夫妇想不出这么个人来。他们家的抽水马桶坏了,也是老漆动手修好的。他们对老漆心怀感激,他们知道打着灯笼满世界找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朋友,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星期六的恐惧还是越来越深了,星期五的夜里小孟上床时会发出一声莫名的怪笑,明天星期六,老漆又要来了。
他们曾经猜想老漆有所企图,可是夫妇俩很快意识到这种猜想对于老漆是一种污辱,他们一个是搞自动化程序的,一个是会计,能对人家有什么贡献呢?他们相信老漆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无所企图,他只是到他们家来处朋友的。夫妇俩都不是那种乖僻古怪的人,他们相信处朋友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他们就是不明白老漆为什么每星期都要来,为什么一来就要坐那么长时间呢?
宁竹设计了几个方案,目的都是想限制老漆作客的时间,有一次老漆和小孟在客厅里聊的时候她抱了一堆帐本出来,说是在替别的单位做帐赚外快,明天早晨就要交出去。她就坐在他们眼皮底下,她以为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但老漆无动于衷,老漆只管说他的政治笑话,他的政治笑话确实很好笑,但宁竹怎么也笑不出来,她对小孟说,没听见炉子上水开了?快去灌水呀!小孟刚要起身,老漆却先站了起来,他说,我去灌。老漆像主人一样冲进了厨房,小孟就半坐半站地看着宁竹,他说,你太过分了。宁竹朝他翻了个白眼,收起桌上的东西跑迸了卧室,宁竹在卧室里独自大发脾气,她把小孟的枕头狠狠地扔在地上,还狠狠地踩了几脚。那天老漆送来了修好的挂钟,老漆走后小孟想把它挂到墙上,但宁竹不许他挂。小孟意识到妻子真的是生老漆的气了。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傻呀?宁竹说,我就差下逐客令了,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人家是直肠子,不习惯拐弯抹角的吧,小孟说,再说他也想不到你会这么烦他?他帮了我家多少忙了,不图回报,他怎么想得到你会烦他?
怎么没有回报?宁竹大叫起来,她说,他把我们的时间拿去了,他把我们的星期六拿去了,别人一星期有七天,我们只有六天,这回报还不够吗?
小孟一时无言以对,宁竹毕竟是会计,她算的帐总是让人茅塞顿开。小孟嘿嘿地笑了一会儿,他对妻子说,你要是实在烦他,以后你就在星期六回娘家吧,我一个人留下来陪他,按照你的算法,我们让老漆拿去半个星期六,不就减少了一半的损失吗?
星期六的脚步来得那么匆忙,小孟一大早就被宁竹推醒了,小孟看见宁竹脸色憔悴满眼血丝的样子吓了一跳,他以为她病了,宁竹说她没病,只是失眠了。我一直在想今天老漆来了会怎么样,我逼着自己不去想,可一闭眼就听见那该死的剃须刀的声音。宁竹说,我受不了啦,我真的受不了啦。小孟觉得问题变得有点严重了,他安慰妻子说,不至于这样,你想想他的好处,你想想他给我们帮的那些忙就不会这样了。宁竹说,我想了,我拼命地想他的好处,可是假如没有那些好处我们不也过得很好吗,我们星期六去山上野餐,去看电影,不出去就在家里看书,就我们两个人,那有多好,他为什么偏偏要挤到我们中间来呢?小孟说,怎么是挤,他是我们的朋友呀。宁竹对朋友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她沉浸在自己的怨艾的情绪里。不行,宁竹突然用一种决绝的语气说,你今天不能留在家里,你跟我一起走。
小孟是那种懂得爱惜妻子的男人,那天他虽然很犹豫,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宁竹。中午离家之前他写了张便条,告诉老漆他们出门了,但宁竹反对他写便条,宁竹说,你告诉他今天有事,那明天呢?明天他一定会再来。小孟说,那不就让他觉察到我们是故意躲他吗?宁竹说,就是要让他觉察到,你不是说他直肠子吗,这回我们就不拐弯抹角的了,就让他觉察到,他是个直肠子,但总不至于是傻瓜!
那天夜里他们回家时看见门口留下了好几颗烟蒂,小孟数了一下,一共有六颗烟蒂,小孟把它们一一捡了起来,再扔在垃圾袋里,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是在把他和老漆的友谊一颗一颗地扔在了垃圾袋里,他的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更奇异的是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扔烟蒂,动作却做得非常夸张非常快乐。小孟其实也说不清那天夜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只记得宁竹在归家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她说,他觉察到了,下个星期六他不会来了。他记得宁竹的声音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他果然没来,等到下午两点他就不会来了,小孟夫妇已经熟知老漆登门的规律,所以当两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们相视一笑,宁竹说,我说过的,今天他不会来了。小孟说,今天他不来了,他把星期六又还给我们了。小孟说这句话用了诙谐的口吻,可是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紧张,有点严肃,一点也不诙谐。
老漆没有来,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显得那么宁静而空旷,小孟一时不知道做什么好,好像这段时间是从老漆那儿偷来的,好像他不忍心随意地用去这段时间,他在家里走了一圈,最后问宁竹,哎,你说我该干点什么?宁竹不无得意地说,干什么不行呀?你看书吧,你都半年没看书了。小孟就拿了一本专业书看了起来,小孟看了一会儿抬起了头,他说,什么声音?我一直听见什么东西在响。宁竹也放下了手里的画报,她说,是呀,我好像也听见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奇怪了,没有什么东西响呀。夫妇俩的目光同时落在了茶几下的隔板上,那只飞力浦剃须刀静静地躺在那儿,没有人打开它的开关,它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夫妇俩知道这只能归咎于自己神经过敏。
小孟不记得那是什么时间了,也许是三点钟,也许是四点钟,反正已经过了老漆来访的时间了,他们突然听见了门外传来的自行车的铃铛声,老漆登门先打铃铛,这也是规律,刹那间小孟愣住了,他看见宁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宁竹惊慌失措地抓住他的手,他还没有明白过来,人已经被宁竹拉进了卧室。
别说话。宁竹捂着小孟的嘴,轻轻地下了命令,不准说话,他敲门不准开门,敲一会儿他就会走的。
小孟觉得自己像一个人室行窃的小偷,心脏跳得快要停摆了,他瞪大眼睛看着宁竹,他想笑却笑不出来,这样不太好吧?他这么嘟嚷着一只手却伸出去轻轻掩上了卧室的门。
老漆在外面敲门,一边敲一边喊着他们的名字。老漆起初敲得很文雅很有耐心,渐渐地敲门声变得急促了,那声音像雷雨一样传到了卧室里,小孟摸着他的心脏部位,宁竹则捂住了耳朵,他们从对方的脸上发现了相仿的坚持到底的表情。他们坚持了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外面终于安静了。小孟先松了口气,他对宁竹说,我们太过分了,他也许知道我们在家里。宁竹对他摇了摇头,宁竹蹑手蹑脚地向窗前走去,小孟知道她去干什么,当宁竹小心地拉开窗帘一角向外窥望的时候,小孟突然预感到了什么,但这样的预感还是来得迟了,他听见宁竹在窗前发出了那声歇斯底里的惊叫。
宁竹后来向小孟描述了她与老漆四目相接的情景,她说老漆站在离窗子一米远的地方打着自行车铃铛,老漆看见她时脸上是一种茫然而迷惑的表情,正是这种表情使宁竹羞愧难当。我后悔死了。宁竹哽咽着说,我想起他的那种表情就后悔,我太过分了,我真是后悔死了。事已至此小孟也无法安慰妻子,他想象着老漆当时的表情,心里也很难受,他说,后悔也没用了,这回他明白了,他再也不会到我们家来了。
老漆后来再也没来过小孟家,星期六不来,星期五和星期天也不来,别的日子就更不会来了。小孟知道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朋友,有很长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六小孟的耳朵里仍然有那些幻听的声音,街上自行车的铃铛声总是能轻易地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下午两点至两点半之间他依稀会听见剃须刀嗡嗡转动的声音。有一天小孟打开那只剃须刀的前盖,看见里面积存了一层厚厚的胡须渣子,就像黑色的灰尘一样,小孟就走到门外,鼓起腮帮把那些胡须渣吹干净了。老漆不再来了,那只剃须刀小孟就归为己用。后来小孟的幻听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每天有多少人在火车上相识,在火车上相识的人们下了火车便形同陌路,小孟与老漆的关系最终还是印证了常识。说来也是巧合,他们后来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有过一次重逢,只不过小孟是上车去外地出差,老漆是来送客,送一群来自东北的客人,小孟猜想那是老漆新交的朋友。
小孟断定老漆看见了自己,老漆的目光好几次从他脸上扫过,但他还是故意把他遗漏了。小孟羞于和老漆打招呼,他一直埋着头,一边偷偷观察老漆,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火车启动。火车启动了,他看见老漆在月台上挥手,小孟知道他不是在向自己挥手,他是在向他的东北朋友挥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