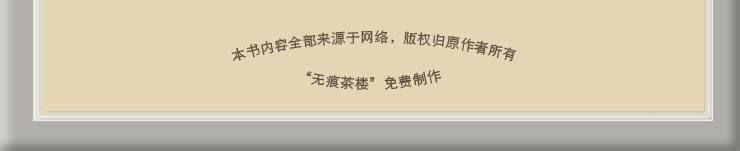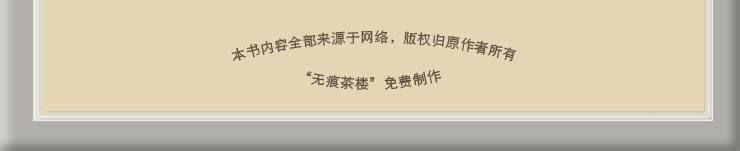|
天赐的亲人
|
|
做女裁缝的儿子,最大的好处是有裁剪合体的衣服穿,最大的坏处是女裁缝没有丈夫,也就是说你去做女裁缝的儿子,虽然有了母亲,也有了草绿色的几乎乱真的军装,但是你却没有父亲。我们香椿树街上的天赐就是这么个幸运而可怜的孩子,我母亲至今还记得女裁缝把天赐抱在怀中走下轮船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下着小雪,我母亲在码头上买黑市米,看见女裁缝抱着一个小男孩从轮船上下来,女裁缝用一条围巾把小男孩的脸包住了,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她以手作伞挡着风雪,也想挡住码头上的人们的视线,但我母亲眼睛很好,她大声地问女裁缝,你抱了谁家的孩子啊?女裁缝装作没有听见,她匆忙地逃走了,就像怀抱着一袋沉重的赃物,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母亲就指着女裁缝的背影对另一个妇女说,看见了吗?女裁缝从乡下抱了个孩子!
天赐就是那个孩子。街上人人知道天赐的名字,就因为他是女裁缝抱来的孩子。大人议论这件事,一会儿说抱的是女裁缝亲戚的孩子,一会儿说是从孤儿院抱来的孤儿,孩子们不关心这一套,他们认为大人透露了一个秘密,秘密的核心是天赐低人一等,他们掌握了这个秘密以后就在街上寻找天赐的踪影,人人都喜欢追天赐,他的怯懦自卑的眼神简直就是一个信号,它示意别人:我很草包,我怕你们,你们来追我吧,你们大家都来打我吧。所以大家都不客气,孩子们看见天赐就欺负他,就连我妹妹,屁大的一个小女孩,也模仿我,拿了个粉笔在街上追天赐,一定要在他背上画一个叉,画不到就跺脚哭鼻子。
说天赐的故事必须剪辑,从他十三岁的时候说起比较像个故事。这一年天赐突然之间发育了,长成一个有点驼背的小老头的样子,我们去阀门厂游泳,看见他独自在更衣间角落里换游泳裤,我们看见了他欲遮还露的羞处,它们雄纠纠的,乌黑而茂盛。让人不由得感到佩服,似乎突然发现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发奋图强,终于干了一件大事。弱国变成了强国。从此没有谁再把天赐当成一个玩偶或出气筒,这当然是后话。也是这一年,天赐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那只地球仪,用我妹妹时髦的语言来说,地球仪改变了天赐的一生,所以天赐的故事简单说来又是一只地球仪的故事。``
女裁缝把地球仪藏在阁楼上。阁楼是她堆放布脚料的地方,她每年都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卖给街上扎拖把的人,她不让天赐上阁楼,怕他把收拾好的布脚料弄乱。女裁缝忽略了那只地球仪,她以为将它用塑料包好藏在角落里,就把一个秘密藏好了,她注意到天赐有几次从阁楼上下来,脸上头发上都蒙着灰垢,天赐说楼上有老鼠,他去捉老鼠,她居然就信了,她忘了天赐已经十三岁,而且早熟,恰好是无事生非的年纪。
有一天故事就开始了。女裁缝在缝纫机前忙碌的时候猛地看见天赐站在她面前,手里抓着那只地球仪。天赐将地球仪转动着,让一块蓝色的标示着海洋的区域对着女裁缝,他说,印度洋上写了个名字,这个毕刚是谁?
缝纫机勤劳的声音戛然而止,女裁缝抬起头,目光掠过地球仪上那个暗淡的名字。哀怨地看着她的养子,让你不要上去乱翻的,她说,这东西没用,我要把它扔掉了。
是地球仪啊,买一个要很多钱。天赐指着印度洋上的那个名字,说,这个毕刚到底是谁?
女裁缝又低头踩响了缝纫机,她说,你问他干什么?跟你没关系的。
肯定跟我有关系。天赐说,他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关系,跟我就也有关系。
女裁缝说,你这孩子太烦人了,没看见我在赶活吗?我没心思跟你说他的事,现在他跟我也没有关系了,我不想提他的名字,茶杯,替我把茶杯拿来。
天赐把茶杯递到他母亲手里,然后他压低声音在女裁缝耳边轻声说,你不说我也猜出来了,天赐嗤地一笑,毕刚就是爸爸,是我——爸爸。
女裁缝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她脸上窘迫的笑容很快被一种愤怒替代了,他不是你爸爸!她说,你没有爸爸,没有就是没有,不能随便拉个人当你爸爸,他怎么能算你爸爸?
天赐的脑袋扭来扭去的,他斜着眼睛看那只地球仪,没说什么,他坐在缝纫机旁边,斜着眼睛,看地球仪上那个人的名字:毕刚1965年9月购于桃花路。过了一会儿,天赐把那行字念了一遍,然后他说,桃花路就是东风路吧,东风路上哪儿有卖地球仪的?从来没见过哪家店卖地球仪。
我不知道。女裁缝说,你别坐在这里烦我,去淘米做晚饭。
天赐对女裁缝一直是顺从的,他拿着淘米箩走到米缸旁边,这时候他突然嘻地一笑,说,我要是姓毕就好玩了,叫毕天赐,毕天赐,多好玩。
你就是没有姓也不姓那个毕。女裁缝说,好好挑石子,昨天你怎么淘的米,差点蹦掉我的牙。
水池在外面的街上,天赐端着淘米箩出去的时候,两只脚在门槛上蹭来蹭去的,女裁缝抬起头盯着他,说,你又搞什么鬼?门槛都让你蹭坏了。天赐说,我一去淘米脚就痒。女裁缝说,什么脚痒,你就是喜欢听那个吱吱嘎嘎的怪声,你这孩子怪毛病多。天赐这时候回过头,看着情绪烦躁的女裁缝,你生什么气?他说,我又没说他是我爸爸,我只是说,他差一点就当了我爸爸。``
尽管女裁缝架子大,对谁都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样子。关于女裁缝短暂的婚姻,街上的人还是知道个来龙去脉。毕刚曾经是女裁缝的丈夫,一个远郊中学的地理教师。他们住在南门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有人在女裁缝的铺子里见过毕刚,说他伏在熨衣桌上备课,一个瘦弱的戴眼镜的人,看上去文质彬彬。女裁缝的顾客都知道新婚夫妇关系不好,却不知道是哪方面不好,女裁缝又不肯说,他们就胡乱猜测,猜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想到是毕刚脑子有问题。谁能想到女裁缝这么精明小心的人,会嫁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呢?后来毕刚的身影就从裁缝铺里消失了,女裁缝死要面子,她骗人说毕刚去援助非洲人民了,但一个惊人的滑稽的消息很快在南门汽车站一带传开了,说毕刚在上海机场精神病发作,他强闯海关,说要去瑞士的什么地方开联合国会议,被抓起来了。像毕刚这么严重的罪行,本来枪毙他也不过分,但因为他脑子有病,有关方面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这都是女裁缝搬到我们街上来以前的事,她以为这么搬个家就把不光彩的历史一笔抹掉了,其实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不肯说自己的事,别人就替你说,这是我们街上的很古老的传统了。人的两个耳朵眼虽然小,但也抵不过几千只大嘴,这么说那么说,所以毕刚的事情最终传到天赐耳朵里也不足为怪。
天赐是个有心事的孩子,他的心事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稀罕知道他的什么狗屁心事,他从十三岁那年开始悄悄地寻访毕刚,女裁缝经常站在她家门口,尖声叫着天赐的名字,她还问我们有没有看见天赐,说这个混帐的孩子,他把淘米箩扔在水池里,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天赐跑到嘈杂拥挤的南门汽车站去了。天赐提着女裁缝买菜用的布包,装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混在候车的人群里,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人口处的那个女检票员。女检票员大概有五十左右的年纪,大概快要退休了,站在那儿懒洋洋的。而且喜欢向人翻白眼,她向天赐也翻了不少白眼,但天赐还是固执地盯着她。天赐知道那个女检票员是毕刚的姐姐。
女检票员向厕所走去,她看见天赐跟上来了。天赐在后面用一种饱满的声音叫她,姑姑,姑姑!女检票员就回头,有点厌烦地看着天赐,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缠人,我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是你姑姑,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是我亲姑姑,但你算是我的姑姑。天赐不依不饶地跟着她,他说,我不影响你工作,你只要告诉我,毕刚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你是她抱养的孩子。女检票员嘴边流露出一丝鄙夷的笑意,她说,你要知道,你跟毕刚没有关系,毕刚和她早就离婚了,你和她现在跟我们毕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要关系。天赐说,姑姑求你了,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求求你告诉我,我来了三次了,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吗?
你别以为找到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女检票员最后松口了,她在一张废车票上飞快地写了一个地址,气冲冲地扔给天赐,她说,我实话告诉你,他脑子不好,他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我不知道天赐为什么要拉我一起去塔镇。那天我母亲让我去女裁缝家拿她的裤子,女裁缝不在家,我看见天赐站在窗口发呆。我问他,你在发什么呆?他忸捏了一会儿,就把那张废车票拿出来给我看了,他向我描述塔镇的那座宋代砖塔是多么值得一看,他让我陪他一起去,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他了。
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毕刚忽然笑起来,说,哪一边也不能帮,各打五十大板,我要是埃及就要出面解决这件事,我要出动航空母舰,我考考你们,假如埃及出军,他们到达黎以前线的最佳路线怎么走?
这回天赐傻眼了,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被一个精神病人考来考去的。我们站在窗外,看着小屋里的毕刚,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让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不愿意被他考来考去,天赐却犯贱,他说,我要是看着地球仪就知道,没有地球仪,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见毕刚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搬出了一样东西。是一只用报纸糊起来的自制地球仪,虽然粗陋简单,但细密的国界线和仿印刷体的字迹使它看上去令人信服。我以前有一只标准的地球仪,不知丢哪儿去了,毕刚把自制地球仪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凭印象自己画的,误差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我记得天赐就是这时候开始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瞪着窗内的那只地球仪,我觉得他又要说什么傻话了,但这次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我考考你。毕刚将地球仪转动了一圈,让西亚东非部分对着天赐,他说,我考考你,埃及的航空母舰怎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黎以前线?
天赐瞪着毕刚手里的地球仪,他张大了嘴,可就是说不出话来。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张大了嘴,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子,向校办农场的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开始飞快地奔跑,他像个疯子一样跑了,把我丢在小屋外面。
荒唐的塔镇之行使我恨透了天赐,我本来就瞧不起他,这次就更加有了瞧不起他的资本了。从塔镇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理发店门前碰到了天赐,他穿着理发店的白围兜出来,想跟我解释什么,我根本就不听他的,我对他说,以后谁要跟你在一起玩,谁就是傻X!天赐像个女孩一样,可怜巴巴地低着头,看我是动真格的了,快快地回到了理发店里。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明白我不要听他辩解。
我说到做到,从大赐十三岁起,我就没有再和他一起玩过。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我的决心,这年冬天我们一家搬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去了。
天赐后来的生活我略知一二,都是我的快嘴的妹妹告诉我的。我必须说明我对天赐沉闷无味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同情,这是我的忙碌的生活造成的。谁都知道天赐没有朋友,我有很多朋友,而时光流逝,孤僻的天赐必将越来越孤僻,我妹妹对天赐的现状无论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能唤起我的兴趣。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女裁缝不寻常的死。我妹妹告诉我进入老年的女裁缝有一天试穿为别人缝制的寿衣,一只胳膊刚刚套进去,人就突然咽气了。这样的死法使人们对女裁缝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寿衣最终她自己穿了。我妹妹说天赐在女裁缝的葬礼上哭得晕了过去,让街坊邻居一致称赞他的孝行,说女裁缝还是有福气,没有白养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天赐是为自己哭,女裁缝一生对天赐的身世守口如瓶,她这一去就把秘密永远封存了。
聪明的读者会猜到天赐的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毕刚。当然是毕刚,多年以后这个丧失了思维和体力的老人来到香椿树街,寄居在铁路桥的桥孔里,几个收破烂的好心人为他提供了残羹剩饭,把这个古怪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群体的一员,他们住在桥洞里整整一个秋天,这期间天赐每天骑车从另一个桥洞中经过,他知道旁边废弃的桥洞里住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他一定曾经见到过独自坐在里面的毕刚,但是天赐不可能认出那个肮脏而苍老的人就是毕刚。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特大寒流将那些收破烂的人驱向温暖的南方,却不知怎么把毕刚留在了香椿树街上。事情说起来有点神奇,那天夜里北风肆虐,风把天赐家的一扇窗户吹开了,天赐从床上下来关窗,看见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天赐就随口对窗外喊,去桥洞,那里暖和。他看见流浪汉回过头来,那种乐观而迷惘的眼神使他觉得似曾相识,老人说,我不冷,只是有点饿。天赐看见老人打开了身边的那只纸箱,然后我所说的那神奇一幕就拉开了,老人捧出一个圆溜溜的东西站在天赐的窗口,他说,这是手工地球仪,误差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小伙子,你给我一碗剩饭,我把地球仪给你。
我们现在无从描述天赐当时的感受,天赐不是个善于表达内心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么一个事实,从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天赐收留了毕刚,当然香椿树街的邻居们大多不知道毕刚这个名字,他们的口径是天赐做善事,收留了一个流浪的患有精神病的老人。街上的孩子不懂事,我妹妹的孩子那天就跑回家,对妈妈说,天赐叔叔把一个疯老头藏在家里!
我知道天赐做了件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香椿树街办事,路过我熟悉的天赐家的门洞。他家的门板新刷了红色的油漆,一张纸夹在门楣下面:小心油漆。我站在他家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文明礼仪,我来到窗前,透过半掩的窗户向里面张望了一眼,应该说我运气不错,一眼就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藤椅上,身穿天赐工厂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手里抓着一瓶孩子喜欢的娃哈哈饮料。他在看电视。尽管事隔多年,我还是从他安详而乐观的眼神里认出来了,那就是塔镇的毕刚。
女裁缝的故居现在住着两个男人,棉布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失了,那台缝纫机不见了,墙上衣架上各种衣服裤子不见了,屋子里面却比以前更显凌乱,我下意识地四处寻找那只地球仪,突然发现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宝贝是在老人的身后,他的藤椅和身体把它挡住了。正是这时候毕刚发现了我,对于一个隔窗窥视的人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指着电视机对我说,美国人又要打南斯拉夫了,我早知道巴尔干半岛三年就要打一次仗,又让我猜到啦!
我忘了我是如何回答毕刚的,也许我就没有和他搭话。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谁去管这等闲事呢。我惦记着去办我的事情,当我骑车经过化工厂那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车从我旁边一掠而过,那个人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天赐。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拖着一只煤气瓶,他没看见我。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我不能确定要是我把他叫住他对我会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不仅不能算是朋友,连街坊邻居都不是了。我看着那个背影风风火火地远去,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要是坦承我发笑的原因读者们会讨厌我,但我当时确实是笑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从小就让人发笑,长大了还是让人发笑,就像天赐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亲人,尽管看上去酷似亲人,但他们终究是来得莫名其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