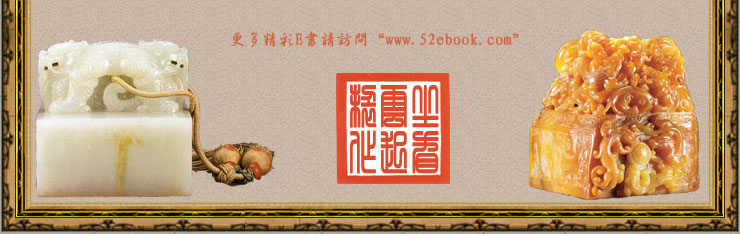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 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注15】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斥责以君为臣纲的程朱理学是“不通大义”的“小儒”。受王守仁心学影响,认为天和人都是“即气即心,即气即理”以为王守仁讲知行合一,是强调“力行”,即把“良知”之“天理”贯彻于事事物物。
【注16】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明亡,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官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1900年6月21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对内宣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1900年1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动来重振国威实力妄想。对于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后人的官方史论)“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是“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为斩监侯,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在社会运动之后,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大阿个哥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后出卖康梁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后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坚定地执行“剿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之于在戊戌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籍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1900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后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劻。虽然,奕劻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于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劻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禧太后鉴于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劻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用,才使他后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详解。
他也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巢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后来,庆王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奕劻作为决策高层人物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隆裕太后,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劻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眷到天津之后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后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