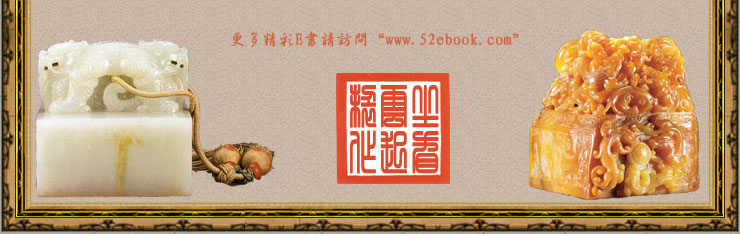传说中黄帝时代,天下大治的景象出现并得出维持,于是出现了瑞祥:屈轶在庭中长出,它会辨忠奸,要是奸佞人进来,它的就指向奸佞之人;凤凰在楼阁筑起了巢,麒麟也在园林中漫步。
出现了这三种祥瑞不久,黄帝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幅美妙的理想图式!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帝尧时代又出现了越裳氏进献的巨龟(到王莽时代被假冒成了纯白雉),帝庭还出现历草--不再也人事有关,而与历法(时间计算)有关。
舜帝是尧帝时代的最大人瑞,经过四位资历长久的政治老人(四岳)的推荐,受用于尧帝。接着,舜帝时代把人瑞与政治治理充分结合起来,高阳氏出了苍舒等八位贤人,时称“八恺”;又有高辛氏的伯奋等八人,时称“八元”;于是舜帝就把他们利用起来。八恺负责农业,八元负责教化。
恺字本意为欢乐,引伸意为恺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平易近人”。八恺乃黄帝之后,因为高阳氏的初始人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元字本意为善良,引伸意为表彰。高辛氏的初始人乃帝喾,帝喾的祖父乃少昊,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玄嚣。
在舜帝的政治谱系里,启用有德的旧贵族就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至少是达到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
之后,人瑞几乎绝了迹。孔丘以为自己是人瑞,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看上他。就不用说周王了,就是鲁国的公也不正眼瞧他,在他死时,只假惺惺地说:“尼父元自律。”(你怎么就这样老了呢!)就完了。以致把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气地说:“活着你不用我老师,现在死了吊丧有个屁用?!”
人瑞是值钱了!如何利用也成了一门大学问。
刘邦即位十年时(公元前197年),打算换掉太子刘盈,让赵王如意上来。吕后一听,急坏了,赶紧去找留侯张良出主意。说是请,实际上是凭老面子硬逼。张良说:“这事儿,口舌不起作用。要改变皇帝的计划,你们就得去请东园公等四位老贤人作太子的客人。因为皇帝一直想请倒这四人,这四人就是不来。”
吕后派人持太子亲笔信去讲四位老前辈,四位老前辈果然赏光,做了太子的宾客,并时时随太子上朝。终于,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计划。
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人瑞是最好不过的奖赏!
历史发展到陈抟进见宋太宗之前,人瑞现象几乎消灭了。
与人瑞相比,更多是人祸。战乱、屠城,成了人祸的最长见场景。赵宋家夺取江山之前五十多年前的血腥屠杀与人相食的当代史记忆,还未消去,所以,对于赵宋家,人瑞的需要远比符瑞更重要!
这成为陈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军阀朱温与刘仁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刘仁恭恐兵力不支,乃在辖区内(今德州至北京间)征兵: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全民皆兵的战术,史称“闾里为之一空”)。为了不让辖区内的男人逃亡,全部给予刺字:一般百姓男子,脸上刺字,“文曰定霸都”;对读书人和做官吏的还好一点,在臂上文上“一心事主”。史称“由是燕、蓟人士例多黥面,或伏窜而免。”采取如此残酷的办法,总共征集到二十万人。
但是,兵员数目虽多,毕竟没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战斗力,与朱温交战多次,无一取胜。随后,全部兵力龟缩到沧州城内。朱温进围沧州城,阻断了一切内外来往。不久,城中发生了饥荒,没了粮食,也没了柴禾。
没粮食吃,就吃人!人饿急了,吃人的本能比野兽还要厉害。一个饿死的人,倚到墙上还没倒下,一群饿急了眼的人就冲上用牙撕咬。人再也不是人了,应该称为“兽人”或“人兽”。人骨头也达到了最高利用程度,尚使还有煮饭(就是人肉)的地方,用得肯定是已死的人骨头当柴禾,只是这骨头比刚死的人骨头稍干一点罢了。
人之不为人,超乎野兽,首先在于他们被困中的生活条件比野兽生存的条件还恶劣。野兽找不到食物可以长途迁徙,但被困于城中的“兽人”要想迁走,无疑于痴人说梦。野兽在实在没吃、没喝的时候,遗传因子告诉它们的只有一个信号:等死。就如现在非洲沙漠的干旱季节一样,一群鳄鱼固守着最后一洼泥水,直至干涸;干涸后,再抗争些时日,生命便结束了。而被围的人,尤其是领袖集团绝对不想死,他们要寻找任何一丝生机。比如说,粮食绝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再吃泥土。记录刘仁恭被围的《旧五代史》“生动”地记载了吃土的后果:“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吃下充当食物的土丸后,人难受呀!十有六七是被坠死,死状很惨,连躺都躺不下,就立着死了(倚在墙上)!!
不到一年,这种残剧再次重演!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反目,被守光拘禁在幽州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而引发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守光染指刘仁恭的小妾,与罗氏私通。儿子与父亲的小妾通奸,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仁恭气急败坏,不由分说给了守光一顿竹板子。守光记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父亲。沧州之围在李克用的帮助下算是解了,但朱温的攻势未减,把目标转向了幽州。
幽州告急,刘守光以救父为名,从外面率兵支援。结果是朱温兵走,而他一言不发地把父亲赶下台去,自任幽州节度使。
父子之不相让如是,就不用说尧舜之间了。尧禅舜继的神话,再一次被证伪!
刘守光拘禁了父亲,其他儿子自然不高兴。守光之兄,沧州守将守文大哭,称:“自古以来,那有儿子以父亲为仇敌的。我家出了这么个匪类,我真是生不如死。”于是率沧州、德州之兵进攻幽州,不幸用计不善反被弟弟活捉,沧德兵败。守光乘机再围沧州。
第二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人吃人发生了。
史载:“沧州宾佐(参谋长)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
城中再次发生大饥荒:一斗米价格达到三万钱,一颗人头的价格也到了一万钱--阵前斩敌也成了一种发财的办法;为了保证战斗力,只允许军士吃人肉,不让老百姓吃--只能如去年一样吃墐土。驴马没了饲料,相遇之后互啃鬃毛与尾巴。最倒霉的是读书人,没有武艺,防不了身,一旦出入家门,就被有力量的强者所屠杀,肉也成了强者的粮食。“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守光…”
这两次重大的相食事件,发生在赵宋家建国的五十多年前,形成了一种“当代史”记忆冲击。怎样避免这样的事件重演,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尤其是由于权力之争发生了家族内部冲突后,“当代史记忆的恐惧”更让皇权阶层焦躁不安。
史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以示对赵炅(光义)之政的推赞。这种超然独立的体制外推赞的现实功效要比体制内的上瑞献祥好得多。也正是这年的春正月,被赵光义贬黜的亲兄弟赵廷美忧悸而死。赵廷美曾扬言,他也效“兄终弟及”的模式,接哥哥赵光义的班。赵光义何许人也?他不会再高喊着遵守宪法了,就此而止。就像大禹一样,不会把位子给别人,而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保证儿子顺利接班,在打击赵廷美之前,他还诬陷自己的亲侄子即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夺权,威胁说:“你要看叔叔我不行,你就当皇帝吗?!”赵德昭不敢担违宪之名,愤而自杀。
陈抟何许人也?北宋安徽毫州真源(今毫县西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不仕,以山水为乐,隐居华山。周世宗以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太平兴国中,两度至京城,为太宗所重,赐号希夷先生。
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