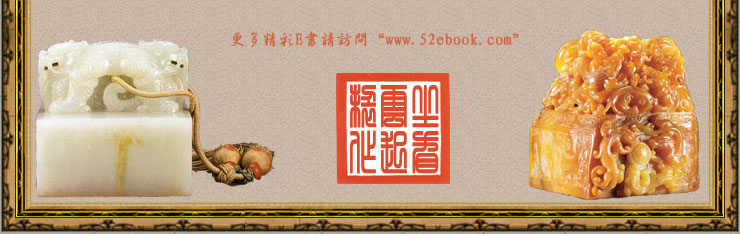误读点评
◎在生活的时下,一方面,我们痛恨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又深蔽于历史迷障,希望出现如古代那的执法如山的好官。殊不知,所谓的清廉,往往是建立在野蛮杀戮之上的!从汉之张汤到唐之来俊臣再到明代的魏忠贤(及其爪牙),酷吏们不但在残害平民,也在残害体制内的同仁。文祸再经典不过地诠释了中国酷吏文化的顽强性——酷吏之害,甚于贪吏之污!
只有人们明白了历史上酷吏文化的本质,才会知道“文祸”并非“史无前例。”
●当新儒学以复兴旗号向天下人宣示他们的理想时,孔儒“上智下愚”的“分层定理”也复活了。殊不知,中国历史残酷的变乱——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庶务,一次又一次打碎了“分层定理”。在下者狡黯乃至坦率地蒙蔽在上者,在上者或是混然不觉,或是迫于大势而隐忍退让。
”上智下愚“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忽视弱势群体的文化,从来不肯精心地(更不用谈认真正)保护弱势群体。奉公守法,成了愚昧无知或不知权变的别称。可悲的是,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写成强盗,或成了强盗的合作者。看看《水浒传》中桃花庄刘太公夹在官与贼之间的窘态,便该明自:不懂历史分析的方法去读《水浒传》,也是中国人读书的一大误区。
于此,乃有重复之叹: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
现代人听来,觉得这个论断十分荒谬,因为不公开审理可以,再严重的案件也得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战乱期或非正状态(如戒解)下,尚有情可愿,要是发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会里,几乎不敢想象。
但是,这却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形成的典籍《礼记》中的刑政规定,<王制>篇称,有四种罪行可以“不以听”即不经审判:
1、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2、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3、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4、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大刑名都是处理与政治有关的所谓非法行为的,特别是对言论的治罪。
《礼记》成于宣帝时,作(编)者分别为戴德、戴圣叔侄。前者之作称为《大戴礼》,后者之作称为《小戴礼》。一般情况下是专指《小戴礼》的。
《小戴礼》综合了战国至西汉初期有关礼的问题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孔子的弟子的论述。虽然《礼记》非孔子之原作,但是也是对孔子礼制思想的精细阐述,同时也表现孔子宗法思想对汉初的影响。
<王制>一篇是在汉文帝时就有了定型,系统记述了封国、爵禄乃至学校、刑政计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又有所发展。<王制>所规定的“此四诛者,不以听”的判例判法,无疑来自孔子对少正卯一案的处理,换言之:儒学后人对少正卯一案的总结,是形成“不以听”的基本根据。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在任鲁国最高司法首长(司寇)、代总理(摄相事)的短短三个月里,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少了少正卯。他给少正卯定的罪有五项:
其一,心达而险;(有知识但心怀险恶)
其二,行辟而坚;(特立独行而又坚持不改)
其三,言伪而辩;(主张与官方不一样的理论又有煽动力)
其四,记丑而博;(总是观注执政阶层的丑闻并且面还很广)
其五,顺非而泽;(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表示赞同并且还施以恩惠)。
在上台的短短七天就对少正卯连抓带杀,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应算得上中国“严打”史上第一个创举性案例。如果仅有七天的时间来搜集五项罪的证据并迅速定性,那么应该是事先早有了准备,也就是说到处置少正卯的时候,只是一个宣判的形式问题了,
少正卯何须人也,竟让一位最高司法首长如此关注并一定要杀之而后快?据荀子与东汉王充的记录和考证,主要是少正卯的学术兴起冲击了孔子的学术地位。“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由于学术之争引发政治倾轧是自然而然之事,它的“活化石”不仅见于上一章所提到的元祐更化那样的事件,也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何况少正卯又是孔子的下级呢!(少正卯为鲁大夫)
尊儒的学者一般都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说法,如民国时期大学问家钱穆称:战国时始行诛士之风,春秋时未见。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证明由于孔子的武断,致使鲁君决定不再信任他;由于他是著名学者又有众多弟子遍及各国(孔子三十岁授徒,二十余年所教甚多),鲁定公顾及自己的声誉不好一下子革除他,只有以“非礼”之行暗示孔子。如本应将郊祭之后的肉分给孔子,鲁君却故意疏忽。
这一重要的失礼细节带来的信息,使孔子确认鲁君不再信任他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别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在到了边境的时候,他还抱着幻想,希望得到鲁君的挽留。为了这一可能的挽留,孔子在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
这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夜。这是让他饱受羞辱的一夜。因为鲁定公并没派人来追他,劝他回去。
有人把鲁定公对孔子的冷淡归于受齐国馈赠女乐并文马的原因,即专于享乐而不听治国专家的意见。其实,反推一下便可知道:一个能够接受专家作司法首长的国君,肯定还会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为他服务,而孔子却不容这样的人出现。少正卯已为鲁之大夫,孔子为了防止少正卯的学说冲击自己的学术地位,不惜动用公法给学术对手定罪。一个国君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为政者的,尽管他以前也颇有作为。
政治生存不同于学问之道,学问上的对手可以用合法的暴力消灭,而政治上的对手则具有相当的反制力。季恒子是父子两代效力于鲁的大夫,自然比孔子更有政治根基,所以他要着力把孔子驱逐出政坛。
孔子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在杀少正卯之前,他为主削平大夫的实力即“堕三都”,与季桓子的利益有冲突。季桓子为“三桓”(鲁桓公之后季孙、孟孙、叔孙三氏)之一的季氏之后,当然要阻止孔子政策的实施。况且定公与“三桓”毕竟有相同的血统呢?后世汉景帝时晁错之削藩,结果殒命,也算“堕三都”理想主义的一个逻辑结果吧!
孔子还算幸运,没有如后来的晁错那样丢掉性命。
无论如何,孔子给学术对手定罪的方法是让人无法信服的。那仅仅可归为一种制造逻辑的艺术,而不能称为公平的法律操作。但,他万万也不会想到,后世因他这一“严打”的伟大创举,把定罪这么一个很严肃的法律技术问题给艺术化了。从判断人表情的“腹诽”到抓人小辫子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把构建良好法律秩序的文化可能全部给打烂了,以致于其间还发生了“史学定罪”的血统论学问。
尽管按学科分类还没有“给人定罪的艺术”这么一个专业,但是它确实已经成为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部分,以致于有了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见它的悠久性与威力性渐成文化特征之一。尽管给人定罪的艺术是儒家发明的,但这并不妨碍法家对它的应用。之于这点,中国的统治(而非政治)文化被称为“外儒内法”,确实精当!
在孔夫子死(公元前429年)后三百六十年的张汤那里,给人定罪的艺术又有了大发展。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汉武帝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想法确属异想天开,皆由于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以白鹿为瑞祥,称它常常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玄了,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认为是瑞物的观点已经确立。
颜异这个人很能干又很廉洁,渐次被提拔到九卿的位置,官拜大农令。刘彻问他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刘彻接受不了反对意见,故而对颜异的言论很不高兴。
皇帝的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有人就根据皇帝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有人告发了他,武帝派张汤去查。
告的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很不恰当,扰民,颜异没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张汤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大做文章,上奏说:
“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叫“腹诽”。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并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也就是,你不说话,只是心里不满也不行。
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高深,但实用性非常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
这确是张汤的绝学,使他从一个侯补御史,一跃成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的这种能为也是法家所崇尚的“恃宠以固位”的方法论(法术)的代表作。
虽然后张汤不幸卷入政治丑闻而迫自杀,而皇帝还是怀念他的“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政治上正确”的补偿,他的后代受到了优待,其子张安世及几个孙子都位居显要,直至封侯。
张汤文化水平不高(曾因此受到丞相汲黯的诟病),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大讲学习。他讲学习方法不是自己学习,而请有学历的人充当下属,史称:“是时,上方响文学,汤决大狱,欲附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然而,张汤无正气可言。为了与替代造假证据害人的手下小官鲁谒居达成攻守同盟,采取非常手段拢络鲁:“谒居病卧…,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这一行动在现在来论是爱护下级的典范,而在那时却成了丑闻;连皇室的人都告发他,指称他与谒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没法解脱,自杀了事。
作为一个法官,他最终因犯法而丢命,但这种现象在古代政治中并不少见。那个因发愤读书并因“覆水难收”一语而暴得大名的朱买臣,也死于刘彻的报复--认为朱买臣陷害了张汤。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张汤还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当然,这是按现代意义套化的。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他给颜异定死罪的狠毒一面,却没看到他为当事人开脱的一面,一定要给皇帝希望轻判的人找到有利开脱的证据,乃至毁灭不利证据。只可惜他的本职工作是法官,而不是律师!
孔子推崇史的道德作用,他做《春秋》以微言说大义,致使“乱臣贼子惧”。这一道德信念影响至深,成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司马迁作《史记》,力图续接孔子的道德版本,只是他远不如孔子那么精细。
多亏他不精细,才给后人留下了诸如仲山甫行迹的那样的历史素材!但司马迁却又有高出孔子、张汤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从血统角度来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把遗传学引入史学领域。
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称以“本纪”,还是给了很高的地位的!)中说:
吾闻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公平地说,这还不叫血统定罪法,因为项羽只是战败而无罪责(那时尚无“战犯”这一概念)。司马迁提供的是一个分析思路。
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一方法论便升华为“史学判刑”的艺术了。在《霍光传》的评语中,班固说:“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很明了:霍光有造反的血传或遗传!
霍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更是成王时代的三个反叛分子之一。霍叔又称“叔处”,武王灭商后,封于霍(今山西霍县),他与另外两位兄弟管叔、蔡叔的职责是监督已被征服的殷人。三人被称为“三监”。武王死后,侄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霍大为不满,便联合管、蔡二人并被监管的纣王之子武庚还有淮夷、徐戎部落,起来反叛。最后,叛乱被平息,管叔被杀,蔡叔被囚,他被废为庶民。
霍光【注1】死后其对立面纷纷上告他家的过失,妻子、儿子、女婿恐惧不能自持,最终走上了谋反的道路。谋反未成而被发觉,整个霍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了霍皇后一人被废而未遭刑事处分外,霍家的人被斩杀一绝,他夫人“(阎)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
【注1】霍光(?-公元前68年)西汉大臣。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弟。初为郎,继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常侍武帝左右,很受武帝亲信。武帝卒,他与桑弘羊等同受遗诏,立昭帝。昭帝即位时只八岁,他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封博陆侯。昭帝卒,又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去,另迎立宣帝。先后执政二十余年。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曾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盐铁会议。
不惟他的家族遭到了毁性打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千余家。”--这是一场政治地震,一场西汉历史上少见的政治地震。
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持续有多长时间,只有确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从班固为霍光做传的语气来判断,到了东汉,这场政治地震所衍生的种种传说还是不断,特别是由此衍生出的故事仍很新鲜。班固采用了一个盛传不衰故事,故事也是一句成语的“曲突徒薪”来源。霍光家族因手握重权,生活方面也更加侈奢,吃喝、车行、建筑各方面无不出尽风头。有一个籍贯茂陵的在京读书人徐福,见到霍家种种行迹,就预言说:“霍家必然败亡。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知道:奢侈使人傲慢不逊,不逊必然会侮辱在上的。侮上,是逆道。再说,权位重要,在众人之上,人们都生除去他们心理。霍家执掌权柄久了,人们更想除掉他。人们都想除掉他,他又对皇上不恭敬。不败亡,等什么?”他为此还给皇上写了信,递了三次,才到皇帝手中。信中的大意是说:“霍家势力大张,都是因为皇上您厚爱所致;为了免使霍家丧亡,您该压压他家的风头了!”
后来,霍家满门抄斩,状告霍家的人也都得到官职或爵位。有人为徐生的言论给皇上写信,说:“臣我听见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客,看见主人的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了柴禾,就劝戒主人把烟囱改成弯的,把柴禾往远处挪。主人不以为然,笑他多事儿。过不久,果然失火了。邻居们奋力拼救,把火灭了。灭完火后,主人杀牛摆酒,请领导喝酒。被烧燎的人坐上席。其余的人各按功劳大小排坐次,但是没请当初劝他改烟囱的人。有人发话了:当初你要听了客人的劝,也不致今天破费牛酒。主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请当初建言的那个客人。茂陵徐福的上书不也是这么回事儿吗?如果当初皇帝听了徐福的话,也不致于破费封官赏爵的官位与土地了,霍光的家族也不致于被诛灭呀!希望皇上能体察徒薪曲突之策的作用,不能只让救火的人居上首呀!”
宣帝刘询明白了这个意思,就给了徐福十疋帛的赏赐,后来又提拔他做了朗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