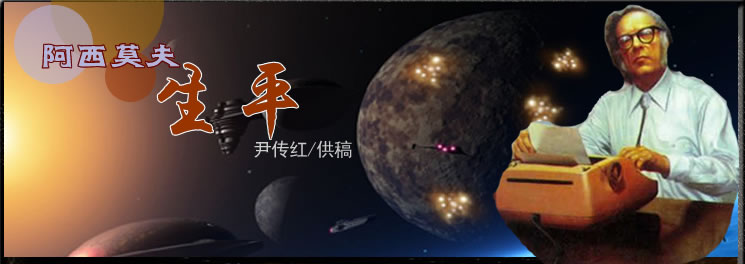 |
 |
|
|
去做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
|
|
我明白,我决不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去做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
“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
1920年1月2日,阿西莫夫出生在原苏联斯摩棱斯克的彼得洛维奇,双亲是犹太人。3岁时,他随家庭迁居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1928年加入美籍。
阿西莫夫生性聪明,记忆力极强,5岁时就在当过会计师的父亲的辅导下开始自学。7岁时,他居然已能教5岁的妹妹念书了。后来,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本小利微,家境并不殷实,阿西莫夫便利用课余时间帮忙照应:站柜台、发报纸、为固定客户传递电话信息…… 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这段经历对阿西莫夫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寻常,小时候又受到严格的管教,再加上从小就承担起家中的一些责任,这使得阿西莫夫具有极强的责任感。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米歇尔?怀特所言:“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将阿西莫夫塑造成了后来那个自觉、自律、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工作狂。在他的一生中,停止写作几乎能够给他带来生理上的痛苦。”
而且,阿西莫夫对科学产生兴趣,也跟他父亲开的这家杂货店有关。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杂货店这个“载体”,阿西莫夫恐怕不会受到流行书刊的启蒙影响,也不可能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科普和科幻小说大师。
 在阿西莫夫的少年时代,美国的公共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具备初级阅读能力的读者骤然增加,于是,各种各样的通俗杂志便应运而生。1926年,有个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卢森堡移民忽然萌生一念:如果把科学知识揉和到惊险故事中去,就能把青少年读者吸引过来。这样,一个以科学启蒙和预测未来为目标的新杂志——《奇异故事》诞生了,这也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科幻杂志。 在阿西莫夫的少年时代,美国的公共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具备初级阅读能力的读者骤然增加,于是,各种各样的通俗杂志便应运而生。1926年,有个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卢森堡移民忽然萌生一念:如果把科学知识揉和到惊险故事中去,就能把青少年读者吸引过来。这样,一个以科学启蒙和预测未来为目标的新杂志——《奇异故事》诞生了,这也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科幻杂志。
创办伊始的《奇异故事》每期都刊载一些科学试题。这些试题以及那些充满幻想的科学故事令9岁的阿西莫夫十分着迷。每看完一期他总是又热切地盼望着能早一天看到下一期。阿西莫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科幻读者就像棒球迷期待双杀或全垒打一样,渴望太空船或新的电子技术能产生奇迹。在和同伴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时,我把手中的玩具枪当成激光枪,去射杀甘尼美星上长着犄角的恐怖怪物。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各位读者可以想象出,脑筋死板、只重视普通常识的家长们,在看见我们阅读原子弹、电视飞弹、登陆月球、火箭等等故事书时的滑稽模样。对他们而言,那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聊故事罢了。”
的确,当时阿西莫夫的父亲是不允许他看那些店里代销的、类似《奇异故事》那样的流行书刊的。在父亲眼里,它们不过是给游手好闲者消遣的垃圾文学,对孩子没什么好处。因此,凡是阿西莫夫要看的课本以外的书刊,都得经过他的检查、筛选。“望子成龙”心切的他甚至认为,儿子应该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温习学校的功课。只要阿西莫夫有一门功课未达到90分,父亲就要对他进行审问;如果在班上的名次下降,等待他的则是更为严厉的盘查。
在很多情况下,阿西莫夫只能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把那些杂志拿过来翻一翻,常常也不过是瞄上一两眼,太不过瘾啦。有一次,阿西莫夫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管制”了,便机灵地反击说,他被禁止翻阅的一些书刊其实父亲就看过,尴尬的父亲则辩称自己是通过看杂志学英语。
“胳膊拧不过大腿”,阿西莫夫只能按父亲的要求办。但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了。没过多久,《科学奇异故事》杂志创刊了,阿西莫夫总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借助刊名上出现的“科学”这么一个极有分量的字眼,终于迫使父亲让步,同意他阅读这份看起来很有教育意义的杂志。
一旦打赢了这一个回合,他又略施小计,让父亲相信了《奇异故事》其实也是一份教育性很强的适合孩子阅读的刊物。从此以后,由于得到了父亲的许可,阿西莫夫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翻阅店里代销的杂志了,那种犯罪般的刺激感也随之消失。但对他来说,令人兴奋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描述的种种令人大开眼界的场景,足以弥补这一个小小的缺憾。
流行杂志为阿西莫夫开启了阅读之门,使他对知识产生了一种渴求,并且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求知和思考、钻研问题的乐趣。这不仅给他带来了学业上的成功,而且还将他引入了写作生涯。
去做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
中学时代的阿西莫夫喜欢独来独往,常给人以傲慢的印象。在展示自己令人惊叹的记忆力并考高分的同时,他还喜欢瞎起哄和搞恶作剧,跟老师们对着干(他的这种闹腾和插科打诨的“习性”,到了大学时代和踏上工作岗位伊始仍在“发展”,并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因此,虽然阿西莫夫的功课很棒,但他却不招老师待见。在他14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还差点断送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事情是这样的:写作课老师在让同学们练习作文时,要求大家写一篇描写性的散文。阿西莫夫听了感到很振奋,因为他刚看过不少19世纪的小说家的作品,满脑子的风物场景。现在好了,可以打着做作业的幌子写篇小说,借以显示自己的才干了。
他打定主意:描绘一个他想象中的乡下的春晨,就以“鸟儿鸣唱、花儿开放”起头。在讲评作文的课堂上,老师问: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念一念自己的大作?话音刚落,自信心十足的阿西莫夫就举起了手,并被请到了讲台上。他不无自豪地吐露出那一个个想象的、显得天真而又幼稚的句子,以为马上就会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不料,等待他的却是哄堂大笑。“狗屁不通!”老师没等他念完就站起来打断了他,大声喝道。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老师苛刻的话语和同学的嘲笑曾经让阿西莫夫感到很伤心,但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也没有让他气馁。就在“出丑”几个月之后,他完成了一篇名为《小兄弟们》的幽默故事,并被登在了校刊上,这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而在这个时期,调皮捣蛋的阿西莫夫也完全能够静下心来学习。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毫不挑剔,什么都想学。他15岁便念完高中,迈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的课堂。课余时间里,他一边大量阅读科普和科幻作品,一边积极思考问题,内心的创作冲动也越来越强烈。18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被放逐的维斯塔》。21岁时,他在著名科幻编辑约翰?W?坎贝尔点拨下,写出了科幻短篇经典《黄昏》并一举成名。
1939年,阿西莫夫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其后又相继取得了该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55年起,他开始担任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从事酶学、光化学的研究。这期间,除了在部队服役的短暂岁月,他一直没有中断科普和科幻创作,并且已经写出了奠定他科幻小说大师地位的几部重要作品:《我,机器人》和《基地》系列。而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些科普作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早期的科普创作实践使阿西莫夫认识到,他不仅喜欢而且也非常擅长撰写科学类题材的作品(而不只是将它们作为科幻小说的情节与对话的陪衬)。1957年,前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深深地触动了阿西莫夫。他痛感美国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落后于由卫星上天所标志的当代科技水平。作为一名科学作家,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尽力而为,使这种差距尽快地缩小,于是便毅然放下早已得心应手的科幻创作,而潜心于撰写普及科学知识的书籍和文章了(直至15年后他才“重出江湖”,再度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然而,创作需要充裕的时间,教学工作显然大大限制了阿西莫夫的创作活动。另外,极有自知之明的阿西莫夫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自己的头脑和专业功底并不差,但自己的前途并不是在显微镜下,而是在打字机上:“我明白,我决不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去做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1958年,他毅然不顾他那时尚未离婚的前妻的反对,告别了讲台和实验室,成为一名专业专家。
这是阿西莫夫事业和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24本书。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