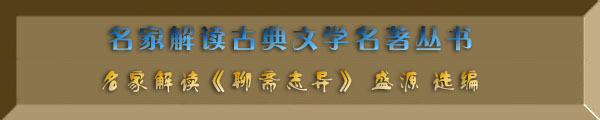聂绀弩 漫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
|
--寓讽刺如针似剑 假戏谑亦真亦幻
一 以“林四娘”作比较 林四娘故事,清初似很流行。《红楼梦》中就有贾宝玉等咏“姽婳将军林四娘”的诗。《聊斋志异》卷三,有《林四娘》篇,与《红楼梦》所咏人物,别是一种身份。
《聊斋志异·林四娘》篇后,附有王士祯《池北偶谈》所记林四娘事, 及林云铭的《林四娘记》。三篇内容不同,而《聊斋志异》一篇独胜。《林 四娘记》中“青面獠牙,赤体挺立”之类描述过多,后虽变为“国色丽人”, 读者已有印象于前,感觉难改。故不足道。兹就《林四娘》篇与《池北偶谈》 所记试作比较。因《聊斋志异》已为人所熟悉,故只引林四娘末尾的林作一 首,其他的文字都不再详引了。
┅┅诗曰:“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 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问禅。┅┅”诗中 重复脱节,疑传者错误。(旁点句为《池北偶谈》所无——引用者)
《池北偶谈》:
闽陈宝钥┅┅观察青州,一日燕坐斋中,忽有丫环┅┅搴帘入曰:“林四娘见!┅┅ 妾故衡府宫嫔也,┅┅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 年国破遂北去(费解——引用者)。妾魂魄犹恋故墟。今宫殿荒芜,聊欲假君亭馆延客。 固无益于君,亦无损于君。┅┅”┅┅自是,日必一至。每张筵,初不见宾客,但闻笑声 酬酢。久之,设具宴陈及陈乡人公车者。十数辈咸在座,嘉肴旨酒不异人世,┅┅酒酣, 四娘叙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如是年余,一日黯然有离别之 色,告陈曰:“妾尘缘已尽,当往终南。以君情谊厚,一来取别耳。”┅┅自后遂绝。┅┅ 程周量会元记其一诗云:“静锁深闺忆往年,楼台箫鼓遍烽烟。红颜力薄难为厉,黑海心 悲只学禅┅┅” 何以说《聊斋志异》胜于《池北偶谈》呢?第一,《聊斋志异》所叙林
四娘与陈宝钥,是很明确的男女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关系明确了就有文
章好写,许多情致缠绵的东西就会随之而生。《池北偶谈》所叙,这一关系 很不明确,所谓“假君亭馆延客”,“固无益于君,亦无损于君”,究竟算 怎么一回事?作品总是反映人类生活的,也就是反映人与人的关系。第二,
《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的身世是非常清楚的,她本人的身世之感非常浓厚, 歌唱“亡国之音”,谈往事“哽咽不能成语”,夜诵经咒,评骘诗词。尽管 作者交代这个人是鬼,但这个鬼却在作品中作为血肉的人而活起来了。《池 北偶谈》虽然也说“叙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等等,但是是抽象的说说, 作者没有使她在作品里活起来。第三,《林四娘》篇,作为作品,从头到尾, 是一个整体。每段文字和前后文字都互有关系,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牵一发 而全身俱受影响,例如所记诗句:“泣望君王化杜鹃”云云,恰好是她的身 世,是她的情感。《池北偶谈》忽叙她延客,忽叙她宴陈及陈的乡人,不知 有何必要。后说:“尘缘已尽”,不知有何“尘缘”;“以君情谊厚”,亦不知有何“情谊”。至于诗,恰好没有“泣望君王化杜鹃”等句,以致“红 颜力薄难为厉”云云,力量也小得多。诗还是诗,但不是作品中所必需的诗 了。这就是说《池北偶谈》所记,是凑缀而成,不成整体。第四,《聊斋志 异》结处说:“诗中重复脱节,疑传者错误”,把整个故事归之于传说,故 卖破绽,反觉真情宛然。《池北偶谈》恰无此意。
《池北偶谈》所记,与《红楼梦》中所叙有相同处,林四娘为衡王(《红 楼梦》作恒王)所宠爱的人。《池北偶谈》写作时间当早于《聊斋志异》, 即较近于原始传说。《聊斋志异》可能是就《池北偶谈》改作的,《聊斋志 异》中每有就前人作品改作之事,有时还有声明。《聊斋志异》一开始就与《池北偶谈》不同:林四娘是“处子”,即非衡王宠姬。是宠姬与不是宠姬, 分别很大。是宠姬,则是旧朝的得意人物,惓怀故国,不足为奇。不是宠姬, 则是一般人;一般人而惓怀故国,惓怀者和被惓怀者的身份都被提高了。这 一改变,同时使作者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对陈林之间的两情缱绻,可以畅所 欲言,不会招致名节或诬蔑前代宫闱之类的非难。林四娘这个人物,也就没 有什么遗憾。回看《池北偶谈》之所以捉襟见肘,吞吞吐吐,恰是被这一问 题束缚住了手脚。末了,加了四句诗,加强了所谓故宫禾黍之悲,使全诗都 更沉痛了。相同句中个别字样不同处,也是《聊斋志异》较好,说不定作者 本人真有此痛。
又卷五《大力将军》篇,与《觚剩》中的《雪遘》篇为同一题材。先读《雪遘》,也觉不坏。但读过《大力将军》之后,再读《雪遘》,把两篇放 在一块儿比较,便觉《大力将军》以少许胜《雪遘》多许。《大力将军》侧 重吴六奇,省掉了叙查伊璜的许多笔墨。《雪遘》两者并重,不分主从,致 成两橛。中幅叙吴六奇如何以军功起草莽,末幅叙查伊璜“益纵情诗酒”, “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离题都远。其次,《大力将军》叙查 伊璜初遇吴时,“厚施而不问其名”(附论中语),一则显出查品格之高; 二则后叙查再遇吴,觉“素昧生平”,遂成奇遇,故能引人入胜。《雪遘》 叙两人初见时“日夕痛饮,盘桓累月”,下文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写,写了也 不会太吸引人了。
此外,甘宁庙神鸦事,《筠廊偶笔》和《滇行纪程》都有记载;洞庭湖神借船事,《子不语》中也有记载。但都不过“记载”而已,无人物,无故 事,亦无描写。《聊斋志异》却用同一传说,写出了《竹青》和《织成》两 篇作品。尽管这两篇在《聊斋志异》中都不算最好的,但总是不错的作品。 诸书所记,不过简单素材,连和《聊斋志异》比较的资格都没有了。
二 《聊斋志异》的画龙点睛与画蛇添足 一篇文章,读到快完的时候,都觉得平平无奇,忽然最后几行、几句甚至几字一点,以前的那些平平无奇的东西,忽然字字生棱,一齐飞起。这种境界,我称之为画龙点睛法,与习用意义也许不完全相合。
《聊斋志异》卷一中有《叶生》篇,述叶生能文而“困于名场”,受邑 令丁乘鹤赏识,丁解任,函招叶来,拟将携之“入都”。叶适病,丁留待之, 叶至,遂与俱行。后丁令其子以叶为师,叶尽心教之,丁子遂入学、中举, 成进士,做了官;叶自己也中了举。丁子出差,顺便送叶返里,事情就叙完 了。这样一篇文章,如果也算作品,是一种何等死气沉沉的平凡作品!下面接叙叶到家时光景:
见门户肖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且骇走。生凄然曰: “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觏,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久 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已成立,行将卜窀穸,勿作怪异吓生人!”┅┅
原来以前所叙随丁入都那些事都是鬼作的。古话说,“得一知己,虽死无恨”, 这篇《叶生》的表现要深得多,死了还要魂随知己!这的确显得有些迷信。 但两三百年前的人,就用这迷信,达到了用现实主义手法所不能达到的深刻 沉痛的程度,使这篇作品成为全书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而且在后面还附了 一篇在全书中最庄严沉痛、唯一庄严沉痛的“异史氏曰”。正文和附论,在 科举时代,对易感的“怀才不遇”者,都是一种催泪剂。因之也就暴露了科 举制度的罪恶,引起了读者对它的憎恨,尽了它的反科举制度的任务,是两 三百年前相当可贵的民主思想。
卷十三《口技》篇:村中来一女子,为人医病,但自己不能处方,需夜 请于神。请神时,自处一室,使人窃听。听见先后有九姑、腊梅、六姑、春 梅、小儿、猫、四姑、小女子和医者自己,各自声音不同,寒暄、问答、嬉 笑、辩论,同时并举,此外还有帘动、椅动、投笔、磨墨、折纸、撮药种种 声音。诸神从来到去,“听之了了可辨,群讶以为真神”。读到这里,我也 “讶为真神”,书中鬼神之类不是很多么?可是与口技什么相干呢?疑心文 不对题,下面几句点题了:
而试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谓口技。特借之以售其术耳。
恍然大悟之后,回想以前所述,真是口技,绝妙的口技。 卷十一,《佟客》篇,叙董生平生慷慨,以“忠臣孝子”自许,好击剑,恨不得异人传授。一日途遇佟姓客人,邀至家:侃侃而谈,客“惟敬听而已”。
夜深,忽闻隔院有监“榜掠”其父,并谓“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生 提戈欲往,佟止之曰┅┅盗坐名相索,必将甘心焉。君无他骨肉,宜嘱后事 于妻子。┅┅生诺,入告其妻。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遂共登楼上,寻弓 觅矢,以备盗攻。”不管父亲了。
这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那种平日夸夸其谈,临事畏缩的人。大而革命,小而日常生活中,每有此等人。但没有最后几句,还以为真有盗劫事,讽刺 意味尚不浓厚,趣味也少。
仓皇未已,闻佟在楼檐上笑曰:“贼幸去矣!”烛之已杳。逡巡出,则见翁赴邻饮, 笼烛始归,惟庭前多编菅遗灰焉。乃知佟异人也。
这几句一补,不但根本没有盗劫,不过客人以“编菅”戏弄之,而平生 慕异人,异人在前,却当面错过,这就成了双层讽刺。意味深长。
试想想,这种作品,如果换一种写法,先告诉读者:叶生已死,到村中 来卖药的是口技艺人,董生所碰见的就是异人,即使也能交代清楚,不知会 消费多少笔墨,而且一定会索然无味。回头再看,方知此种作法之妙。
也有一种和上述情况相反的境界:写好了一整篇,处处都好,却因为最 后几段几句或几字,舍不得割弃,致与全文抵触,大则破坏前此所辛苦塑造 的形象,小则也成为可有可无,没有则更好的冗赘。这种情况,其严重者, 可谓之画蛇添足。《聊斋志异》作者自是文章圣手,但有时亦难免此弊。
卷二《婴宁》篇,是一篇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婴宁是一个极美的天真少 女的形象。《荡寇志》写陈丽卿,其最成功处或即脱化于此。这篇作品,如 果只写到结婚而止,真是题无剩意,态有余妍。不幸后面有这么一段:
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邻西家,女每扳登其上。┅┅一日,西邻子见之,凝注倾倒, 女不避而笑。西邻子谓女意已属,心益荡。女指墙底,笑而下。西邻子谓示约处,大悦。 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 水淋窍也。┅┅
试问《婴宁》一篇,何须有些节外生枝!特别是那些污秽字句,真是“刻划 无盐,唐突西子”!《金瓶梅》里有一段短文,数来宝似地数潘金莲的眉儿 眼儿,以至全身。这种文字若移赠林黛玉,将是何等恶札(有些《红楼梦》 续书正是如此作,所以可恨)!不是说林姑娘没有形体,而是说,某种人物 应用某种笔墨形容,用得不得当,则是对人物和乃至作品的伤害。
《聊斋志异》于收煞处造成冗赘的不少,因所关较小,故不多列举。
三 对话 在《聊斋志异》之前,我国小说如《水浒》、《金瓶梅》、《西游记》等雄篇,对话都具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魅力。但那些都是白话小说,所 用语言,本近日语,要逼肖说话人的身份、口吻,还比较容易,而且这些又 都是长篇,一个人物反复出现多次;人物也多,可以互相衬映,对话的性格 化也不算太难。而《聊斋志异》却是文言文,特别对于写对话,就难免不是 一种极其笨拙的工具。即使是文人学士,说起话来,也未必真有那么多的之 乎者也,何况一般人?更何况闺房儿女?作品又是短篇,没有许多回旋反复 的余地,对话非一开始就具有特色不可。又无许多人物对比衬映,要显出性 格,自然就更难。
《聊斋志异》的对话,首先是恰切,即某人在某一场合,一定会说那一句或几句话,换别的什么话都不恰当。例如卷三《织成》篇,叙柳生醉卧船 上时,曾咬过织成的袜子,而未见其面。后遇一女子,作者必需在此告诉读 者,她就是织成,必需通过本人来说明她是织成,这织成开口第一句应该是 什么话呢?女趁柳生看她的袜子的时候笑曰:
耽耽注目,生平所未见耶? 只此一句,便觉更无他语能如此恰当而且灵巧。又卷五《阎王》篇,叙小叔 劝悍嫂改行:
嫂怒曰:“小郎若个好男儿,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 一作声,自当是小郎大好乾纲,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
写悍妇对小叔的口吻何等逼肖! 对话的恰当性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看来是与作品所需要的意思相反或者不甚相干,但却正是作品所最需要最恰当的。卷七《邵女》篇,叙邵女 劝平日气焰甚高、此时气愤在胸的大妇去与在外与妾同居而偶归的丈夫打招 呼,大妇不得已而为之,见面时该说句什么话呢?“归耶!”两字也可了事, 表示了她的不情不愿。而篇中却是:
汝狡兔三窟,何归为! 八个字,可把一个一面低头、一面又不肯放下架子的大妇的身份神态都活画 出来了。又卷三《庚娘》篇,写一丈夫在江中见邻舟少妇似其妻子,少妇亦 看他,他要问那少妇是不是妻子,该用什么话说?《聊斋志异》写道:
急呼曰:“看群鸭儿飞上天也!”少妇闻之,亦呼云:“馋■儿欲吃猫子腥耶?” 盖当年闺中之隐谑也。
想来没有比这一特定夫妇所独有的“隐谑”更能以最少的笔墨在这场合收到 同样效果的了。
对话很容易写得干燥无味,如果只照作品情节所需要的那样写的话。作 品是生活的反映,对话也必须有生活气息,才能更好地为作品服务。比如说, 织成一上来就说:“我织成娘也。”金生高声问:“汝庚娘耶?”何尝不也 把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读者读了这样的对话,也许不会感到太不满足。问 题是读到了上引的《织成》、《邵女》、《庚娘》等篇的对话之后,便觉得 “我织成也”之类真是味同嚼蜡了。因为这种对话没有两者之间历史关系, 生活气氛。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说话的。不,应该反过来说,《织成》、《邵女》、《庚娘》篇中的那种对话,是联系着历史关系,人们在实际生活 中,就是那样说话的,不过作品提炼得更加精致罢了。
《织成》、《庚娘》等篇中的人物的历史关系,作品在前面已经写了, 读者早已知道,提出之后,也就容易理解。有些作品,前面既未提及,后面 也不交代,光听一段对话,也能看出人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同时,对话本身 也非常生动。如卷二《珠儿》篇,叙珠儿向父母述赴冥中见亡姊经过:
昨托姜员外夤缘见姊,姊呼我坐珊瑚床上。与言父母悬念,渠都如眠睡。儿云:“姊 在时,喜绣并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浣绫子上,姊就刺作赤水云。今母犹挂床头壁,顾念 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凄感┅┅(按:这段对话在整个作品中有小问题:珠儿并非此 家儿,对过去事不应如此熟悉。但作为对话,却是绝妙的。)
又如卷五《狐梦》篇:
婢入曰:“二娘子至。”见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 新郎颇如意否?”女以扇击背,白眼视之。二娘曰:“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妹畏人数 胁骨,遥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谓我当嫁僬侥国小王子。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 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
在作品中读到这样逼真而又趣味盎然的姣憨儿女们的絮语,真不禁令人要狂 喜雀跃。那怕只读一遍,也会留下深刻印象。其所以如此,是作者无端生出 什么姜员外,什么喜绣并蒂花,就血痕绣作赤水云;怕痒,骂她他日嫁多髭 郎之类的事。这些事在情节上都不是必要的,但类似的事却是在生活上谁都 可以碰到,经常反复,富有趣味和特色的。对话之难,推而言之,作品之难, 就在找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一写进作品,如果用之得当,就没有不生动的。 再举几例。卷二《口技》篇:
三人絮语间杂,刺刺不休。俄闻帘钩复动,女曰:“六姑至矣。”乱言曰:“春梅 亦抱小郎子来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呜之不睡,定要从娘子来。身如百钧重,负累 杀人!”┅┅即闻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远迢迢招猫儿来!”既而声渐疏,帘又 响。满室俱哗曰:“四姑来何迟也!”有一小女子细声曰:“路有千里且溢,与阿姑走尔 许时始至,阿姑行且缓!”┅┅
又卷三《翩翩》篇:
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 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来未?”曰:“又一小婢子。” 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城笑曰:“而家小 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值得寒 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 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前篇有旁点处,都是凭空结撰。四姑来就四姑来,六姑来就六姑来,只此几人,问病开方,有何不可?却从四姑六姑,想到各有婢女,六姑且有小 儿,小儿又有猫儿。又从六姑婢女抱怨小儿体重,四姑婢女抱怨路远而主母 缓慢。所有这些与问病开方毫无关系。但因之却显出了四姑、六姑的身份。 既有此身份,就可能是真懂医理,能开方的人。而主要的则是迫近了生活真 实。人们,这里是说旧时代的妇女们,就是这样过生活的:串门子,走亲戚, 拖泥带水,絮絮不休,正因为迫近了生活,所以在窗前窃听的人,才“讶为 真神”,信其药方,想不到竟是一种口技。后篇更是全体空灵。有什么翩翩, 有什么花城娘子,更有什么小江城(小江城为下文与翩翩之子结姻的伏笔, 但也是一语可了的事)?但不如此写,就看不出岩穴之中,也正有人在过着 生活;自然也就不成其为作品了。《聊斋志异》就擅长写各种各样的小儿女 们的琐细絮语。似乎越是琐细,作者越有兴趣,也写得越好。这就告诉学习 写作的我们:一个作家,一定要观察、体验、掌握这种在生活上随时出现的 极其琐细的东西,把它们当作木屑竹头而储积起来。当然这并不是教你写那 些琐细事物的本身,而是说无论写什么大作品,描写怎样了不起的对象,如 果能把那些琐细的东西运用得当,那木屑竹头就不再是木屑竹头,而是随珠 卞玉,光芒四射,使作品活起来,飞起来。《红楼梦》那种雄篇,里面该有 多少琐细的东西呀!
《聊斋志异》中的对话之妙,当然不限于以上所举,也不限于这一方面。
特别是卷四《狐谐》,卷七《仙人岛》,卷八《司文郎》等篇中的对话,真 是字字生棱,不可逼视(三篇就作为作品说,《狐谐》最完整,《仙人岛》 头重,《司文郎》尾赘)。但诙谐嘲讽之类的对话,本容易见长,更容易领 会,这里就不再提了。
四 化腐朽为神奇 文章境界,有一种叫做化腐朽为神奇。也没有看见谁有过确切的解释,这里就只好以意为之了。
化腐朽为神奇,应该有各种各样。 一种是像前面谈过的《叶生》篇,写叶生在京里中了举回家,一直到了家,看见了妻子,全篇已快要结束了,都是极其平凡的,甚至是恹恹无生气的。及至妻子开了口,说他早已死了,原来他自己是鬼,却连自己也不知道。 这样一来,前面那些平凡文字,登时改变,变得无比的深刻和沉痛。化腐朽 为神奇!
另一种,是平凡而且琐细,谁都经验过,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把它写进 作品里去,而一写进去,就会变成绝世奇文、绝世美文的。如卷六《小谢》 篇,写陶生遇鬼事:
生寂不动。长者翘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女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轻批颐 颊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骤起叱曰:“鬼物敢尔!”二女骇奔而散。┅┅夜将半,烛而寝。 始交睫,觉人以细物穿鼻,奇痒大嚏。但闻暗处隐隐作笑声。┅┅俄见少女以纸条燃细股, 鹤行鹭伏而至。生暴起诃之,飘窜而去。既寝,又穿其耳。┅┅长者渐曲肱几上观生读, 既而掩生卷。┅┅少者潜于脑后,交两手掩生目。瞥然去,远立以哂。┅┅ 除了那两个女的是鬼以外,这样的生活——穿睡着了的人的耳鼻,掩人眼睛或者被穿被掩,谁不反复过多次,像这种调皮的少男女在一块儿时的无 邪嬉戏,谁又不曾经历过、看见过或听说过呢?可是自己不会写,也很少看见人写!化腐朽为神奇!这段文字,是书中最美的章段之一,若与《小翠》 篇同读,令人心情有返老还童之感。
卷二《婴宁》篇,写王子服与婴宁相叙:
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生曰:“此上元妹 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女曰:“此大细事,至 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 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 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这真是个傻大姐(这里应曰傻小姐)似的人物!说也奇怪,凡是带点稚
气的人物,写入作品,多数场合是活泼生动(霍生),痴憨的女性更是如此。
《荡寇志》中刻画陈丽卿的性格之所以得到部分成功,就有可能是从《婴宁》 篇窃取了痴憨这一点。从婴宁,我们得到的印象不是痴憨之类,而是纯真、 姣贵、高洁和什么都比不上的美和可爱。这是又一种:化腐朽为神奇!
还有一种:作品需要形象,作品里的人物需要性格。作品的形象和人物 的性格,通常被视为与议论之类是不相干的乃至是对立的东西。反之,议论, 总是被形象和性格所排斥,无论是作者直接说出来,还是借作品中的人物说 出来。有些大作家不肯放弃议论。《约翰·克利思朵夫》中有几十万字的议 论,《战争与和平》辟有专章来发议论。对不对且不谈,总之,作者也好, 读者也好,都没有认为那些议论就是形象或人物的性格;而且也没有人认为 是作品的主要部分。《聊斋志异》则不然。卷九《乔女》篇,叙乔女奇丑, 夫死后又奇穷。孟生欲娶为继室。女曰:
饥冻若此,从官人得温饱,夫宁不愿?然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 官人何取焉?
这已是小发议论了。后来孟死了,“女往临哭尽哀”。孟子幼,无戚党, 村中无赖携取其家具,谋分其田产。女闻孟有友人林生者,乃踵林门而告曰:
夫妇、朋友,人之大伦也。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 已心许之矣。今身死子幼,自当有以报知己。然存孤易,御侮难。若无兄弟、父母,遂坐 视其子死家灭而不一救,则五伦中可以无朋友矣。妾无所多须于君,但以片纸告邑宰。抚 孤则妾不敢辞。
这是一段主要议论。后林因被无赖所挟,不敢过问。女乃“锐身自诣官,官 诘女属孟何人。”女曰:
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虽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则道路之人可听也。 就是这三段议论,乔女的性格非常突出,也非常形象化,这作品的主要部分 就是由这些议论构成的。再说一句,这一篇,是全书中思想性最高、战斗性 最强的作品之一,所提出的问题:男女之间,除了夫妇关系,除了性的关系, 而且高于那种关系,甚至也高于朋友关系,应当还有某种关系存在,乔女就 证明这一点。在两百多年前,是非常尖端的民主思想。作者非常赞叹他所创 造的这个人物,他的“异史氏曰”:
知已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何知而奇伟如是!若遇九方皋,直 牡之矣!
议论,一般不是形象,更不是性格,是不消说的。但在一定的场合,和 一定的人和事结合,却可以成为形象乃至性格。《乔女》篇就说明这一点。 有人读到这篇作品而感到它缺乏形象、缺乏性格的么?有人觉得它是和《金和尚》、《续黄粱》那种作品一样缺乏形象和性格的么?如果没有,那就要 问,它的形象和性格何在呢?回答只能是这几段议论,因为这几段议论确实 是作品的主要构成,删去这几段议论,它就不成其为作品。这一问题极有意 味,他日当另论之。这里只指出这一点:用议论塑造人物,构成形象,而且 成为作品的中心,是一种最特出的化腐朽为神奇!
化腐朽为神奇。知道有这种境界,也知道某些作品或某些章节达到了这 种境界。但以怎样的努力可以比较直截达到这种境界,却一无所知,自然也 无话可说。一般的生活、修养、练习,恐怕也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我正在学 习中,在有所领会之前,如有高明指教,那是欢迎之不暇的。
五 奇想
《聊斋志异》所写的东西,虽说表面上说是鬼是狐,实际上却正是人们 的生活,有的还是经常反复,谁都经历过的生活,像前面谈到过的某些例子 一样。这是一方面,或者是主要的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就量说是次要的 方面。即,不但不是经常反复的生活,甚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但一 写进作品里去,读者并不感觉它不是日常生活里所有的而不能接受,刚刚相 反,而是认为是一种新奇的生活,虽然在现实生活难以碰到或根本不可能有, 但那种意境,却是生活中所应该有的。这就在无形中提高或丰富了人们的精 神生活。这种东西,不知别人叫它什么或应该叫它什么,我一时无以名之, 姑名之曰:奇想。
书名《志异》,除了一些有闻必录的记载以外,凡经作者组织过的作品,都不能没有作者的想象在内,有时也不能没有作者的奇想在内。《聊斋志异》 里的奇想是很多的,这里只举几点在作品里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又极有意义或 趣味的东西。
卷十一《白秋练》篇,叙慕生在逆旅诵诗,窗外有女子窃听。后女母来告,女因听诵诗而成病,非结为婚姻不可。生不能自主,未即谐。一夕,母 送女置于生榻而去。
移灯视女,则病态含娇,秋波自流。略致讯诘,嫣然微笑。生强其一语。曰:“‘为 郎憔悴却羞郎’,可为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怜其荏弱┅┅女不觉欢然展谑,乃 曰:“君为妾三吟王建‘罗衣叶叶’之作,病当愈。”生从其言,甫两过,女揽衣起坐曰: “妾愈矣!”再读则娇颤相和。┅┅后生因不见女而病。女来,又吟王建前作。
生曰:“此卿心事,医二人何得效。┅┅试为我吟‘杨柳千条尽向西’!”女从之。 生赞曰:“快哉!卿昔诵诗余,有采莲子云:‘菡萏香连十顷陂’,心尚未忘,烦一曼声 度之!”女又从之。甫阕,生跃起曰:“小生何尝病哉!”┅┅
女从生北归,以坛载湖水,“每食必加少许,如用醯酱”。最后, 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嘱曰:“如妾死,勿瘗,当于卯午酉三时,一吟 杜甫梦李白诗,死当不朽。候水至┅┅宜得活。”┅┅ 诗在佳人才子小说中起很大作用,是周知的。但那都是自作,一唱一和之类。此是诵古人所作,并能当面医病,什么诗医什么病,则为任何小说所 无。古有陈琳檄能医头风,杜甫诗能医疟疾的传说,脱化而用到恋爱上来, 更觉优美。本篇在全书中也是写恋爱关系的最美的篇章之一。
卷八《司文郎》篇,叙王生应试,遇一余杭生,极狂悖。一日与宋(司 文郎)于寺廊见一瞽僧卖药,宋谓其“最能知文”,应以文请教,会余杭生亦至,王遂向僧“具白请教之意”。
僧笑曰:“是谁多口,无目何以论文?”王请以耳代目,僧曰:“三作两千余言, 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 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 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已作。┅┅僧 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生惭而退。数日榜放,生竟领荐,王下第。宋与王走告僧。┅┅俄,余杭生至,意气发舒, 曰:“盲和尚┅┅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 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 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 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谁曾见过以鼻嗅文,而且嗅得那么有声有色?但试想想,如 果不用此法,怎样能挖苦科举,挖苦科举制度下的得意者到这样痛快淋漓的程度呢!真是 奇想,极可贵的奇想。
卷十二《苗生》篇,叙几个酸丁游山,又联句,又各诵闱作,互相赞赏。
苗厉声曰:“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 众有惭色,又更恶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 去。┅┅
酸丁不自知其丑,更不自知某种行为讨人厌,有时使咬牙切齿,无可奈 何。遽置之于死,固太过分,然此不过小说家一时快意之作,不能当作真事 看待。契诃夫也曾有一短篇,叙一作家有急事正拟出门,忽来一女客,坚请 他听诵己作,文又臭又长,主人再三请停不获,性急无奈,乃用大斧将女客 砍死。其意与《苗生》篇正同。但苗生本虎化之人,被迫复化为虎,其噬人 原不足怪;契诃夫作,其人亦常人耳,常人因不耐听文而至杀人,夸张性就 更大了。
卷十一《嘉平公子》篇,叙某公子为娼鬼所迷,家人“百术驱遣之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谕仆帖┅┅‘椒’讹‘菽’,‘姜’讹‘江’,‘可恨’ 讹‘可浪’。女见之,书其后云”:
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自此遂绝。这篇作品有很深乃至很多的寓意。比如说,女子出嫁后,发 见丈夫不如意,应有脱离自由,也是其中之一。但白字可以却鬼,却是奇想。 作家在不拿笔时,也无异于常人。拿起笔时,他就变成他所要创造的那 个世界的主人,要照他自己的意志安排那个世界。不用说,纵然做了主人, 也不可能是很自由的,因为客观存在不因他的意志为转移,而他的意志要受 客观存在的制约。但若干程度的自由是有的,而写神话之类的作品的作者, 比专写现实题材的作者的自由要大得多。因为鬼神妖异之类不能尽以人事律 之;若能尽以人事律之,就不是鬼神妖异了。这中间就容许有些杜撰,也就 是创造。《聊斋志异》的奇想是从这里产生的。若说鬼神妖异若写得与人事 无关或完全与人事不类,读者就无法理解了。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是题外的话。
六 文章从矛盾中出来
《聊斋志异》的《乔女》、《侠女》、《绩女》,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
这三篇中的三个人物,都是本身有着不能解决的矛盾,所以极其容易地构成 了作品,显出了人物。乔女之言曰:
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已心许之矣。 “固拒”而又“心许”,就是乔女的矛盾,文章就在这矛盾中。如果她不“固 拒”,改嫁孟生,事情便了了;若不“心许”,则孟生身后事,与她何干? 正因“固拒”而又“心许”,所以成为乔女,所以成为《乔女》篇——接触 到男女间比较复杂的问题,富于思想性的作品。侠女之言曰:
养母之德,刻刻不去于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第也。为君贫不能 婚,将为延一线之续。
“相报在床第”,则无戏可唱;不“为延一线之续”,则无话可说。要这样 又要那样,所以成为侠女,所以成为《侠女》篇。乔女以“不事二夫”为贤, 侠女则唾弃此种观念而为侠矣。这是另一种思想性。两女都封建(乔以不嫁 二夫为贤,侠以人宗祀为忧),又都以其轻微的封建突破更严重的封建(男 女不相闻问和女子必须守贞的封建),又是相同的矛盾。绩女之言曰:
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若不速迁,恐陷身情窟,转劫难出 矣。┅┅
若不“堕情障”,何处得见绩女;若不怕“陷身情窟”,则亦书中其他人物 耳,何以为绩女,何以为《绩女》篇?老子之言曰:吾之大患,在乎有身(未 对原文)。不管原意云何,可以说这是被压迫者的想法。若压迫者,则正因 为有身,才能压迫他人,何足以患?
推绩女之意,当曰:女之大患在乎有性,有性斯有情,不免“偶堕情障”,
被男性所玩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的女性的想法。 以上所举,是矛盾之存在于人物本身者。不过存于人物本身的矛盾,也是客观社会的矛盾以及人物与外界的矛盾的反映。没有以“不事二夫”为道德的客观社会,就没有乔女的矛盾。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道 德,也没有侠女的矛盾。没有玩弄女性的男性中心社会,也没有绩女的矛盾。 矛盾是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如《王者》、《席方平》、《崔猛》、《田七郎》、《向杲》、《商三官》等篇;或男女之间的《窦氏》、《姚安》、《武孝廉》、《云翠仙》等篇,则是写出了矛 盾的两方面,是非善恶的两方面,并已发展为鲜明的乃至血腥的斗争,那是 显而易见的。也有写出了两方面,但未表现为什么太尖锐的斗争的,如《司 文郎》篇中的司文郎、盲和尚所代表的反科举与余杭生所代表的科举力量之 间的矛盾,《张诚》篇中母子之间的矛盾,《珊瑚》篇中姑媳之间的矛盾,《胡四娘》篇中胡四娘与庸俗家庭之间的矛盾,《连城》篇中的连城、乔生 与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虽然也如火如荼,但比起上述的那 些矛盾,却和缓一些。至于《劳山道士》篇中王七与道士之间,《仙人岛》 篇中的王勉与芳云姊妹之间,《佟客》篇中的主客之间,《老饕》篇中的邢 德与老饕之间的矛盾,就更和缓了。
个人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往往只写个人方面而没有代表另一方面的人物 出场。如《叶生》、《贾奉雉》、《于去恶》等篇。但读者会明了其中人物 的对立面是科举制度,却没有代表科举制度的人物,而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受 难而显出科举的不合理、显出读书人与科举的矛盾来。
也有看起来写得如火如荼的矛盾现象,因为作者没有理解或没有交代那 矛盾的原因,没有根据那矛盾现象作较深的掘发,所交代的原因不是原因,尽管读的时候,也觉得写得不错,但读后回味,就会发现那种现象是不是矛 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都不可知。如《马介甫》、《江城》两篇,写了怕 老婆的故事,而为什么这样怕老婆,至少,我个人还至今不得其解。《马介 甫》篇根本没交代,《江城》篇说是前世孽缘,显然不能使人满足。
另外有些根本没有矛盾的,但读起来也有吸引力,也能表现出人物来。 首先,因为这书是“志异”的,里面的“异”,总多少有点引人入胜。其次, 作者在里面使了一些手法,如在《婴宁》篇中在婴宁身上加上憨、好笑、爱 花等等特点,这人物就活起来了;《白秋练》篇(其中有极微小的矛盾), 加上诵诗医病,就给读者以新鲜感觉而印象加深了;《狐谐》、《狐梦》、《翩翩》等篇写了极生动的筵宴诙谐,本身已自可喜了;诸如此类。但也有 是作者制造了一点人为的小矛盾而成篇的。如《王桂庵》篇,无论桂庵与芸 娘之间,桂阉与江蓠之间,芸娘与江蓠之间,都没有矛盾。文章起初是从相 逢不相识、别后又无从询问而来,接着是从“门前一树马缨花”的梦之可“异” 而来,其后是从桂庵炫富、江蓠拒婚而来,最后是从桂庵戏言、芸娘信以为 真而来。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是真正矛盾。前面说过,有的矛盾,只写一方 面。《王桂庵》篇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呢?不是。《叶生》、《于去恶》等篇 的主角都在受难,这受难是制度使然的,所以是矛盾。《王桂庵》篇中没有 人受难。如果也可说是受难,那是出于误会。误会之类是不能当作矛盾的。 不能说这篇作品不好;桂庵、芸娘、江蓠,都有性格。这就是好处。但在书 中,在以恋爱为题材的作品中,总不是使人首先提起的。
书中有两种作品:一种接触到了别人所看不到或看到了不怎么注意的问题,反映了客观社会的真实矛盾。书的思想性、战斗性是表现在这些篇章里 的。另一种是写得很美、很高,甚至生活气息很浓,却不一定接触到什么问 题。光看后一种作品,也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足;及至看了前一种作品,不 免以不接触什么实际问题为憾,回头又以前一种作品有的未能写得如此优 美,如此富于生活气息为憾。这是作者的矛盾。这个矛盾和以上所说的矛盾 都不同——上述的矛盾,文章从之而生;作者的矛盾却限制产生更好的文章, 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地达到同等高度的文章!作者的这一矛盾,有机会当另 论之。
七 向题材追索作品所需要的东西 叫孩子发一封信。
就是这样一件事,简单得很。这样一件事,如果写进作品里去,自然有时就像上面那样几个字就可了事;但有时却必需写得很长。这件事,在作品 里没有什么大作用,只是交代一下过程,就不必加以什么描写;如果是有大 作用的,它在作品里处于很重要的地位,而作者要读者对这件事有强烈的印 象,那就非加以描写不可。叫发信的是谁呢?孩子是男孩是女孩、多大多小? 时候是白天夜晚,天气是阴是晴?信是给谁的?贴了邮票还是要去买邮票? 诸如此类,┅┅作者尽可以向它追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特别是在写真人真事的场合,事件本身必定伴随着 许多真情实景,那些真情实景说不定自己会跑到笔底来。至于鬼神妖异之类 的题材,那就不可能出于生活经验,不可能真是作者所熟悉的。这种场合, 作家到何处去追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呢?这是愚问。鬼魅并不存在,它本身就是人的创作。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神的时候,同时也就创造了鬼魅。而 人除了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创造鬼神之外,不可能用别种方法创造。不言可知, 作家除了按照人的状态、人的生活描写鬼神以外,也不可能用别种方法描写。 那么,向鬼神的事情上追索作者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向人的生活里面追索。 但这样说,不过就其基本点而言,若以为在任何细节上,鬼神与人都毫 无二致,岂不是人并没有创造鬼神,《聊斋志异》也无异可志了么?必须是 一面按照人的生活描写鬼神,这才能够写,写了能被理解;另一方面又赋予 鬼神以若干和人不同的特点(如能变、前知、来去无踪等),这才算写的是鬼神而不是人。
《聊斋志异》善于从任何一件简单事情上追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 卷四《促织》篇,写村中少年以自己的蟋蟀与成名的相斗争时:
视成所蓄,掩口葫芦而笑。因出已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作, 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 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以试猪鬣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俄见小虫 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 这样一段文章,如果在不需要的场合,本篇下文“试与他虫斗,(他)虫尽靡”,就可包括。在需要的场合,就写了少年的轻浮态度,成名的心理 过程,虫的形状,相斗的情景,战胜后的得意状态。许多文字奔赴而来。何 必有此真人真事?又何莫而非真人真事!这都是作者即景生情,从生活中追 索出来的。
又卷一《叶生》篇,叙叶生返家时:
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且骇走。
只 12 个字,对当时应有情景,何等逼肖!如果写妻出,见生后即骇走,何尝 不也了此一段公案?只添了一个“簸具”,就不但写出了妻的平日生活的勤 苦,与上文“门户萧条”相调协,而且生出“掷”之一事,使“骇走”有声 有色。又如上文虽写“簸具”,见生时,骇走而不“掷”,则恐怖之态,犹 未画尽,自不用说。
卷八《钟生》篇,叙钟生求准新娘上山去参拜久已出家的岳父,求他解救“弥天之祸”。一般看来,去就是了,还有什么另外的文章可作?《聊斋 志异》却写新娘:
乃一夜不寐,以毡绵厚作蔽膝。各以隐着衣底。
下文叙相见时,而坐前悉布沙砾,密如星宿。如不敢择,入跪其上,生亦从诸其后。┅┅夫妻跪良 久,筋力俱殆,沙石将压入骨,痛不可支。┅┅
前后呼应,就显出了女儿对于父亲的理解,平日父女关系的情况,请求的不 易和对请求准否的担心和一定要请准的决心以及高僧的身份等等许多复杂情 况。而更重要的是使读者觉得像真有此事。如果没有这段描写,则前后所写 都是一笔表过,没有高潮,不能构成作品(《钟生》篇本属平凡之作,但那 是另一问题)。
卷十《席方平》篇,叙冥王命锯解徐体。这是重刑,已用过许多文字烘 托、描写。锯时,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这觉 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堂上传呼,令合身来 见!二鬼即推复合,曳使行。席觉锯锋一道,痛如复裂,半步而踣。一鬼于腰间出丝带而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
这段文字之妙,不仅在描写锯刑的过程,而且在从锯刑关合到受刑者的 “大孝无辜”,行刑鬼卒较冥王尚有人心,显示了阴曹之黑暗。从锯想到心, 从“锯锋曲折”而想到“其痛倍苦”,被辟之后,时而“两身”,时而“合 身”,都好像真有其事。这不能说是生活经验,没有人能有这种经验。这是 文心,是作者从这一特定事件上想象出来的,今谓之想象力。作家固然需有 丰富的生活经验,但个人的生活经验无论怎样丰富,对于生活总体说,总是 有限的。因之就需要根据已有的经验去推知那未曾经验的生活。向所写的题 材追索它所应有的、可能的东西,使它看来好像是理有固然、事所必然一样。 这种本事是作家所应具有的。完全没有这种本领的作家,大概没有。但本领 越大,他所能涉及的题材范围就越广。《聊斋志异》当是有较大的本领的。 有人把某种作品谑称为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毫无血肉的作品大概也难 碰到,而什么是血肉,也无人确说。这一节和前面“对话”一节,我自以为是在向这一问题探索的,不过还只刚刚开始。
(选自《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