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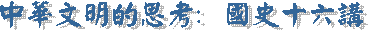
樊树志
|
康熙的文治(2)
中国和俄国的尼布楚条约谈判,康熙皇帝任命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席代表,同时委任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参谋官随同前往。他们两人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成为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康熙皇帝还大力支持西医的传入中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向他讲解西洋科学知识,由于他的患病而中止,却为白晋、张诚提供了向他讲解西洋医学知识的机会。康熙病愈后,仔细阅读他们编译的西医讲义,非常赞赏。他希望传教士推荐西洋医生前来中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在给大学士明珠等人的谕旨中说,鉴于南怀仁年事已高,听说澳门有同南怀仁一样熟悉历法的人才,希望你们会同礼部,请南怀仁推荐,同时推荐精通医术的人才。
南怀仁神甫察觉到这是一个传教事业的契机。在利玛窦以后,耶稣会士能够得到朝廷重用,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长,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清朝初年,汤若望神甫、南怀仁神甫接连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负责人。但是由于西洋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在理念方面的差距,使南怀仁感到,继续向中国输入西洋的天文历算,可能会影响传教事业。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的兴趣,使他预感到,派遣传教士医生可能是有助于传教事业的最佳选择。双方的共同愿望,促成了西学东渐的中心,由天文历算转向了医学。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高潮。
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精通医术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北京,进入宫廷。其中有颇受康熙器重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法国耶稣会士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康熙皇帝御医、外科医生——意大利耶稣会士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宫廷药剂师——葡萄牙耶稣会士魏哥儿(Miguel Vieira),在京行医三十二年的外科医生——意大利修士罗怀中(Giovanni Giuseppe da Costa)等人。他们在中国的行医活动,为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功不可没。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康熙后期,由于所谓“礼仪之争”,显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障碍。康熙皇帝派遣耶稣会士白晋作为他的特使,随同罗马教皇特使铎罗(de Tournon)回到欧洲,解决礼仪纠纷,但是没有成功。铎罗代表教皇宣布在教会中禁止中国的礼仪,使得双方矛盾激化。清朝方面则采取了比较灵活务实的对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一道皇帝谕旨宣布,西洋人必须领取内务府颁发的“印票”(执照)后,才可以在中国传教,没有领取“印票”的传教士必须离开中国,但是具有西洋技艺的传教士不在驱逐之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帝在接见福建的传教士时,再次重申传教士中的“会技艺人”不在驱逐之列。他还授意罗马教皇派来的神甫,写信给教皇: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无以图报,今特求教皇选拔具有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等学问的传教士,来中国效力。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一个大国君主的宽容风度,没有盲目排外,为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康熙时代,西方传教士受到了礼遇,得以深入宫廷,深入上层政坛。不仅如此,在皇帝多次南巡中,沿途都把会见天主教传教士作为议事日程。传教士普遍满意于皇帝对他们的关注,皇帝给传教士留下了令人喜爱的形象。耶稣会士白晋两次受到接见,并且陪伴南巡,使他以后有机会向皇帝介绍欧洲的科学和医学,对皇帝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来白晋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传教士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欧洲,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最辽阔、最富饶,管理最完善,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1645—1716年)、伏尔泰(1694—1778年)、魁奈(1694—1774年),都受到了影响。给他们影响最深的是,清朝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择最有教养的人为官,使中国因此而避免了欧洲世袭贵族政治的弊端。他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欧洲从未实现的柏拉图理想——由哲学家皇帝统治的国家。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根据这些记载,对18世纪的中国作了这样的评论: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