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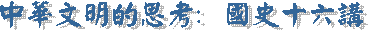
樊树志
|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1)
比数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向政治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汉元帝虽然多才多艺,精通书法、音乐,会作曲、演奏乐器,但毫无政治才干。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汉成帝更加沉迷于经学,任用刘向整理儒家经典,就是突出表现。他一味按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包装自己,仪容端庄,不左顾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气象,却不知如何执政。当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批评他作为皇帝的“失德”时,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经学,诚恳地接受,以显示纳谏的雅量。
如此众多的人在经学中讨生活,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与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持续不断的争论。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何谓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所谓古文,是指战国时代东方地区的文字,汉代已经不通行。这些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大体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即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敬献这批“古文经”,希望把它们也列为太学的钦定教材。从事校勘古籍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