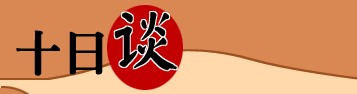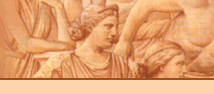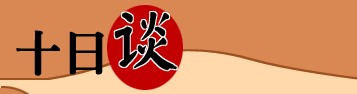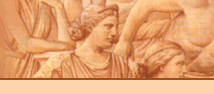|
最尊贵的太太小姐们,为了给你们消遣解闷,我担当起这一个艰巨的工作来;承蒙天主的照应,当初我在这部书开头所许下的诺言,现在总算全部完成了。我认为,天主赐给我帮助,并非由于我自身具有什么功绩,而是全靠你们虔诚的祷告。所以我首先应该向天主谢恩,其次就要感谢你们;从此我就可以放下我这支笔,让我疲乏的手休息一下了。不过我很知道,我这些故事并非什么不可侵犯的东西,免不了会遭受别人的非难--我在第四天的开头也曾提到过这点--因此,在搁笔以前,我想对哪一位太太小姐或是别人可能提出的责问,简短地答复一下。 也许有哪位太太小姐会说,这些故事里涉及男女的事情太多,不是正经的女人所应该说、或应该听的。我否认这一点,因为只要措辞妥当,天下是没有什么事情讲不得的,而我自信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得体。 就算你们指责得对吧(因为我不想跟你们争论,情愿让你们占上风),那么我还有许多现成的理由可以作答辩。第一,即使书中的叙述有什么地方近乎猥亵,那么这原是决定于故事的性质,凡是有见识的人,用平心静气的眼光看一下,就会承认,我要是不把故事改头换面一番,那就没有旁的方法来叙述了。假使文章里面,偶然有一两个名称或字眼有欠文雅,叫你们听来不堪入耳--因为你们这班自命正经的女人把语言看得比行为更重要,只想在表面上装得规矩,而骨子里并不是这样--那么我这样回答:一般男男女女整天都在说着"洞眼"啊,"钉子"啊,"臼"啊,"杵"啊,"腊肠"啊,"什锦香肠"啊等等的这一类话,人家可以这么说,那么为什么偏不容许我这么写呢。再说,我这支笔照理该和画家的笔享受同等的权利。画家可以画圣迈克尔斩蛇,圣乔治杀龙,画里的人用枪也好,用刀也好,都随他的便。不但这样,他还可以把亚当画成男的,夏娃画成女的,画那为了人类得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时他让耶稣脚上钉着一枚钉子,有时又让他脚上钉着两枚钉子,为什么偏要对我加上种种束缚呢? 况且大家也知道,这些故事并不是在教堂里讲的,在教堂里,才用得到洁净的字句,才应该怀着圣洁的思想,尽管在一部教会史里,可以找到不少类似我那些故事里的事迹。这些故事也不是在哲学学院里讲的,哲学家跟别人一样,凡事都要讲究一个体统,更不是在什么修士和哲学家聚会的地方讲的;这些故事都是在花园里、在游乐的地方讲的,听故事的人年纪虽轻,却都已成人懂事,不会因为听了这些故事就此误入歧途;何况当时即使是最有德行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把裤子套在头上,冠冕堂皇地走到外面去呢。 再说,这些故事也跟天下任何事物一样,能够使人受害,也能够使人得益,这完全要看听故事的人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谁不知道,根据钦奇利翁尼和史科莱奥以及许多别的人的说法,酒对于健康的人是无上妙品,可是对于发烧的病人,酒却是有害无益的东西,我们难道因为发烧的病人喝不得酒,就抹杀酒的价值吗?谁都知道,火的功用大极了,人类不能一天没有火,可是火有时也会烧毁房子,村子,以至城市,难道我们因此就怪火不好吗?讲到武器。也是这样,我们要想安居乐业过日子,就必须用力用枪来保障;可是刀枪往往也能杀害人,这不是刀枪不好,而只能怪坏人借了刀枪来横行不法。 卑鄙的小人怎么也不能从好的方面领会一句话里的意思,金玉良言对他们完全没用;反过来说,有德行的人即使听了一句并不是正经的话,也不会因之就减损了人格,正象泥土不能沾污太阳的光辉,地上的肮脏不能玷污美丽的青空一样。 天下还有什么书、什么语言、什么文字比《圣经》更圣洁、更有价值、更受人敬崇呢?可是偏有许多人把《圣经》曲解了,因之害得自己和别人永堕地狱。每一样东西总有它的好处,如果用之不当,难免发生许多弊病。我所讲的故事何尝不是这样。如果有谁听了这些故事,因而起了不好的念头、做出不好的事来,这也是无从阻止的事,不说故事本身或许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是一篇好好的故事,一经歪曲和牵强附会,也会变成错尽错绝了。假使有谁愿意从故事里吸取有益的成份,那么这部作品是不会叫他们失望的。这些故事是为了一定的读者而写的,只要读的时间适当,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书不但有益,而且十分得体呢。 谁家小姐喜欢朝晚祷告。谁象奶奶喜欢蒸糕做饼去孝敬她的忏悔神父,请她们自便吧,并没有谁希罕她们来读我的故事;虽然这一班女圣徒有时自己也不免说出些好听的话、做出些好看的事来。 有些太太小姐也许会说,要是把书里的故事删去几篇,那也许会好些吧。说得对。不过我是无能为力的,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下来。你们应该叫那些讲故事的人把故事讲得规矩些,那么我写下来的自然也规矩了。如果有人以为这许多故事不但是我写的,而且是我编造的(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尽管这些故事并非篇篇文雅,我也并不以此为羞耻。因为除了天主,世上再没有哪个大匠能创造出件件都是完美无疵的作品来。拿查利大帝为例吧,他首先册封了"派拉亭骁士",可是也只封了十二个骑士而已,他终究没法召集那么多骑士可以编成一支军队。世上的事物形形色色都有,哪里能够强求一律呢。一块良田,不管怎样勤于耕种,稻麦里也还是找得出荆棘和莠草来。 再说,我这些故事多半是对你们这班心地单纯的姑娘讲的,如果我费尽心力、专门去阐述什么精深渊博的事理,讲一套文绉绉死板板的话,那我真是愚不可及了。翻开这本故事集,你们尽可以拣喜欢的看,不中意的你们尽可以跳过去。为了免得读者上当,每篇故事前面都有一段述要,把内容点明。 又有些人准会认为有几篇故事太长了。那么我再一次回答他们:哪一个手边有着正经事,却丢开不管,来读这本集子,那么即使是读很短的故事,也是件愚蠢的事。自从我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脱稿,前后已经隔了好一段时光,不过我还记得,当初我是把这本书献给闲暇无事的太太小姐们的,我并非是为别人而写的。你如果读书为了消磨时光,那么,只希望达到目的,决不会嫌故事太长的。三言两句把话说完,这对于大学生是适宜的,他们研究学业,要把光阴用在有益的方面,不能随便浪费。但是大太小姐们,你们却不是这样,除了恋爱,就无所事事,你们既不必赶到雅典、波伦那、或者巴黎去留学,那么不妨跟你们说得琐碎详细些--不能把你们和那些高才博学之士一般看待。 我料想你们之中一定又有些人会这么说:这些故事里戏谑诙谐的成份太多了,似乎不是一个庄严自重的人所应该写的。她们出于这样一片好意,关心我的名誉,我应该向她们致谢--而且已经致谢了。但是对于她们的指摘,我要这样回答:我承认我是自重的,而且也一向为人所看重;可是对于那些并不看重我的女性,我干脆说,我并不庄重;不,我的骨头是这样轻,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你想,近来神父讲道、谴责世俗罪恶时,尚且尽说些笑话和戏言,那么我写这些故事原是为了给妇女解闷,里面有些笑话什么的,就更不足为奇了。如果担心她们会因此笑坏了,那么只消把耶利米的《哀歌》、 救主的受难、曼丽·玛大琳的哀哭等书本打开来,就马上把她们治好了。 此外,毫无疑问,又有一班人会因为我在有些地方写出了神父的真面目,就说我含血喷人。对于说这种话的人,我们应该原谅他,因为要说她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别有用心,那可叫人难以相信。谁不知道那些神父是好人,他们因为敬爱天主,所以不甘于清贫;每逢蓄水池里的水满了,他们就转动起碾磨来,却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要不是他们身上全都带着些羊臊,那真是可人意的伴侣呢。 话虽是这么说,我承认,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的舌头说不定也是这样。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判断(逢到我自己的事,我总是尽可能避免夹杂自己的主见);可是不多天以前,我的一位芳邻对我说,她觉得我长着全世界最甜蜜的嘴巴,是美妙的舌尖。说真的,她对我这么说时,这部故事集子快要写成了。对于那班攻击我的人,我的答复到此为止,不再多说了。 每一位太太小姐,读了这些故事,尽可以自由发表她的意见和感想;我呢,写到这里,就要搁笔了。我衷心感谢天主,承蒙天主的帮助和引领,我花了几年心血,总算了却一件心愿。 可爱的太太小姐们,但愿天主的仁爱和安宁与你们同在;要是你们读了这些故事,觉得多少有些获益,那么请别忘了我吧。 [《十日谈》(一称《咖略特王子》)的第十天,
亦即最后一天,至此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