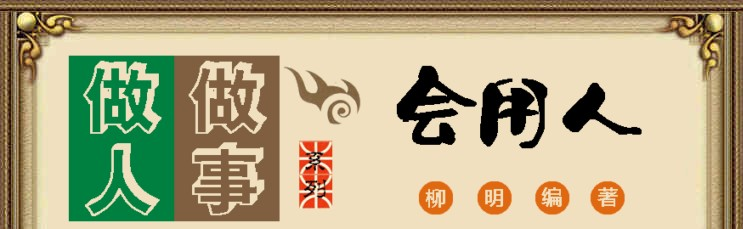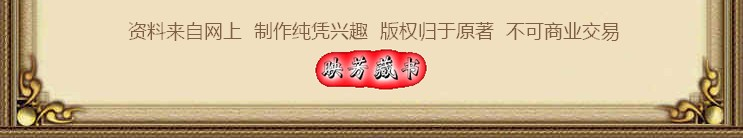唐太宗是个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美名的皇帝。他曾问魏征:“人怎样才能不受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宗深以为然。但太宗在纳谏过程中,自我中心意识也时时露头。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妆排场要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征直言谏明。太宗到后宫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话,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臣直'。魏征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特向陛下祝贺。”太宗这才消了气。其实皇后还是用巧妙的恭维话解决了问题。
唐太宗到了晚年,批评也不大听得进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先后去世。他跟大臣们议事,常常是夸夸其谈,务必压倒对方为止。刚强高傲,日胜一日,以致生活上好色自戕,竟服食方士丹药,政事上又有多处失误。
为什么同是一个唐太宗,却前后判若两人呢?唐太宗曾因群臣不肯进谏而问过魏征。魏征回答说:“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伎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魏征这里只是有保留地从唐太宗脸色变化这个表面现象来说的,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唐太宗在执政之初为了保住江山,除了自己的励精图治外,还需要文武官员为他效劳,因此,不平等待人不行。后来,他的翅膀硬了,江山坐稳了,他的帝王思想也就大大膨胀起来,俨然是一个行为万世师、言体万世法的皇帝顶峰。集思广益的“耳顺”被阿谀奉承的顺耳声所代替。自己既然那么正确、英明、伟大,还要别人啰嗦干什么!于是,“一言堂”的匾额也就这样挂了出来。
唐玄宗早先是个有为的明君,他励精图治,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他那时所任用的宰相,都是敢于提出自己意见的人。虽然接受时对一些尖锐的批评有时也难以容忍,但他毕竟明白,这是为他好。所以他对人说,我虽然瘦了,但天下人都肥了,国家富强了,这就是纳谏的好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可以集思广益地得到很多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好主意,这样便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因一个人思考、决策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理化。唐玄宗的前半生就是因为坚持了纳谏,才使唐朝实现“开元之治”的。但是,后来随着事业有成,有了一定权威以后,他慢慢就不重视倾听别人的意见了。开始是可有可无,逐渐变得不耐烦,最后干脆把纳谏之门关死,从此,他成了目不明、耳不聪的昏君,因为他听到的只是包围他、封锁他、顺着他心说的那些顺耳之言,看到的也只是他喜欢看的那几个人,于是李隆基、杨国忠这样的人物就应运而生成为“宠臣”了。闭目塞听的结果是他被小人坏人包围,成了昏君。不久就成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由明君向昏君的转变就是由纳谏到拒谏开始的。因此,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领导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小事。唐朝有一位学者说:“谔谔能昌唯唯亡。”更把纳谏提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