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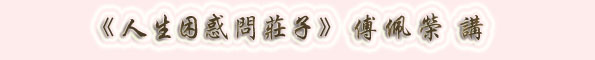
第七讲.上下级相处的艺术 上下级相处的艺术
|
|
傅佩荣:今波,你好!
主持人:“叶公子高”的“叶”字,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读音?
傅佩荣:是的,它念“shè”,“叶”是楚国一个县。楚国在春秋时代,认为自己跟周朝分庭抗礼,所以自称王。周王底下的诸侯,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但是楚国的官,如叶公,就比其他诸侯国高一级,一个县长也称公。
主持人:通过刚才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在古代,做臣子的压力也是很大啊。
傅佩荣:古代是讲君臣关系,君的权力很大了,可说是为所欲为;做臣子的,奉命之后,非完成任务不可,不然提头来见。在刚才所举的“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内热了受不了”,就是一例。事实上古代的这种关系,在今天没有这么严重,今天的上级跟下属的关系,算是相对的关系,在古代则是绝对的关系,是完全不平衡的、倾斜的。庄子举了几个例子来比喻国君。他说,侍奉国君,就跟马夫养马一样,对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竹筐给它装尿、装屎,但是有一天,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马夫看到了,蚊子在叮马,这还得了,要保护它,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它不知道有蚊子叮它,马夫是帮它的忙。这一惊吓之后,立刻把前面的辔头挣脱,把人踢伤了,发疯一样地跑掉了。可见,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心意,用疯马的样子来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则是把国君讲得像老虎一样。
主持人:有的时候就是上面的人不理解你,其实你是为了他好啊。
傅佩荣:是啊,庄子把国君(上级)比喻为老虎,我们现在说伴君如伴虎。他说,一个养老虎的人,每天照顾它,照顾久了之后,老虎看到养它的人,也会有亲切感,因为你一来就有食物吃,就有好处了。但是养老虎的人很紧张,不敢给它吃一整只鸡,不敢给它吃活的东西,怕老虎凶性大发,因为老虎吃的东西都是处理好的,它就忘了自己是很凶的老虎,如果你给它整只鸡或者整块肉,它一下子就发挥它的兽性了,恐怕连养它的人都要遭殃。你看,庄子用这种方式来比喻上级。
主持人:其实,不光是在国君身边当差难,只要是在有上下级区分的情况下,好像这下级就比较难做。清朝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县长,字都不认识,他每次写数字写到“七”,最后一笔总是往里一勾。下属就跟他说,老爷,您这个七字写错了。县长就不高兴了,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老子“八字”好,你是当卫兵的命,我是当老爷的命。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下级该怎么办呢?
傅佩荣: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生下来就是富贵命,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儒家对于这一点说得比较多,儒家认为,你不喜欢上级怎么样待你,你就不要这样对待下级。你现在是下级,不喜欢上级怎么样对你,将来你到了上级的位置之后,就要想到这一点。
主持人:这个观点如果放到孝道当中,就有一个说法,叫不养儿不知父母心。所以,这是不是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傅佩荣: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在《庄子·徐无鬼》里有个故事。徐无鬼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由于女商的安排,从山上下来,去找魏武侯。魏武侯看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有名的隐士。徐无鬼和魏武侯谈了之后,魏武侯非常开心。女商非常奇怪,对徐无鬼说,先生究竟对君侯说了些什么?我一向告诉君侯的,从远处说,是谈《诗》、《书》、《礼》、《乐》,从近处说,是谈《金板》、《六弢》,见于行事而大有效验的不计其数,而君侯从来没有开口笑过。我们这些大臣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大王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你怎么今天跟他一谈,他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有什么秘诀啊?
主持人:对啊,他讲了点什么?
傅佩荣:徐无鬼说,我跟他谈怎么样相狗、相马。古代社会的娱乐很少,他就赛狗、赛马,这时需要有人会相狗、相马,知道这条狗是上等的,这匹马是上等的。徐无鬼跟魏武侯谈论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东西。
主持人:这不就是纯粹技巧性的东西吗?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傅佩荣: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大臣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讲生活上的话,都是讲门面话,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平常的生活。徐无鬼接着又说,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流放的人了——这个人离开国家几天后,看见认识的人就很高兴;离开国家一个月后,看到曾在国内见过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离开国家一年以后,看到像是同乡的人就很高兴。这不是离开故人越久,思念故人越深吗?长久居住在旷野中,听到人走路的脚步声就高兴起来,更何况是有兄弟亲戚在身边谈笑呢!很久没有人用真实的言语在君侯身边谈笑了啊!我现在跟魏武侯谈话,只是把他当作平常人。这样一来,他反而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自己跟别人相处,非常自在,不需要摆架子,不需要说门面话。
主持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对君王是充满了同情的,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被流放的人,非常可怜,犹如孤家寡人,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们。这样想想,是不是当上级也挺不容易的?
傅佩荣:确实如此,因为上级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他上面还有上级,他也有他的压力,他只好把他的压力转嫁给他的属下,这样一来,做下属的应该怎么办呢?自古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还得想起“换位思考”这个关键词,有时当上级的,压力其实比下级还要大,他也不容易,活得也很累,甚至比下级更累。这样一想,我们可能就觉得,上级,尤其是经常提出苛责的上级,也变得不那么可恨了。
傅佩荣:没错,有时说不定他接了他的上级一个电话脸色就变了,上级对他的要求,他根本都看不到对方,马上就要去做许多事情,那我们作为他的属下还可以直接看到他,互相沟通,他说不定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样地换位思考的话,就比较容易从他(上级)的角度来替他设想。
主持人:要是能够和上级沟通,说明这个上级应该是个不错的上级,我们就怕遇到那种蛮不讲理、很难沟通的,那应该怎么办?
傅佩荣:在这个时候,庄子只能够说,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但是迁就不能太过分,顺从不能太过头。你一旦又迁就又顺从,到最后完全没有立场。上级如果走偏了,你跟着他走偏,将来如果出了事,你第一个倒霉。
主持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跟儒家的一些观点似乎不太一样,在儒家的观点当中,如果看到君王昏庸,作为臣子一定要直言进谏,这才是责任。可是您刚才说到顺从,即便他是一个不太好的领导,也要去顺从,您觉得这合理吗?
傅佩荣:在庄子看来,他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我先要保命。如果我直言进谏,国君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有什么保障的。第二个,直接对抗达不成什么目的。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他说不定免你的职、罢你的官。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命;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先顺着你,尤其是直言进谏,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庄子还说,我对你很好,别人问到你的时候,我就说一些溢美之词;我如果对你不太好,别人问你我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说一些溢恶之词。美就是说好话,恶就是说坏话。人很难避免“溢美、溢恶”,往往按照个人情绪、喜不喜欢这个人而定,庄子建议我们不要有这两种缺点,最好选择实实在在的话来说,说多说少都不行。庄子也了解,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困难,上下级关系的紧张。他的观点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任务,又不要添加自己任何的情绪,或者制造一种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主持人: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印象当中,似乎儒家更注重实用,而道家希望的是无为,但是在刚才庄子关于上下级关系处理的观点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实用,而且比儒家的原则显得更实用。
傅佩荣: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庄子的时候,要经常讲到司马迁的话,他说庄子这个人虽然学老子,但是“其学无所不窥”,什么书都看。庄子本身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百姓,只做过小小的公务员,但是他对于上层,那些大官、国君之间的关系,了解得比谁都清楚。换句话说,我们读《庄子》有一个好处,你不用自己去做一件事,就知道那件事情复杂的情况。庄子也说,人的社会总要运转,国君再怎么样不好,国家不能够没有国君,一定也需要各级大臣来做事情,那么如何让国家机构顺利运作,目的是要让老百姓不要受苦。这一套思想,一般人比较少谈,事实上它才是庄子真正精彩的部分。也就是说,我可以向世俗提出各种看法,让世俗机构运作起来,至于我要保护我自己,我自己隐居、逍遥、与道相处,那是我的另外一种秘诀。可见,庄子对自己和世俗分得很清楚。
主持人: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庄子给我们的建议是非常明确的。庄子之所以有如此明确的观点,是不是跟庄子所处的环境有关,就是那时,他所听到或者见到的坏领导、坏君王实在太多。
傅佩荣:他也举了很多例子,如果照儒家的做法,有的是忠臣,有的是孝子,下场都很惨。这种故事举多了之后,就觉得应该找一条可以活命,又可以把事情办完的路。庄子就在这个地方下工夫。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了解庄子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有很多人生的困惑,凭什么问他呢,他又怎么回答我们呢?
主持人:这样说的话,我们更愿意听听庄子能够给我们更加具体的操作办法,譬如,过去很多忠臣,因为直言进谏,最后被昏君给害死了,所以感觉忠臣老是没有好结果。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所谓的领导,同时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傅佩荣:庄子举的很多例子都非常有趣,譬如,有一个人长得奇形怪状,身体残缺,他替国君做事,久而久之国君觉得这个人非常正常,因为他的脖子很粗,结果国君看他看习惯了,见到别人,就觉得别人脖子太细。这个人跟国君在一起,国君不觉得有任何压力,同时又很信赖他。可见你要让上级信赖的话,需要智慧,整个庄子的思想,重点放在智慧上面。譬如,他如果像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他如果不注重威仪,你就跟他一样不注重威仪;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要把国君当作一个主动的对象,好比是两个人跳舞,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然后在关键的时刻,再给他一些暗示,让国君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你没有给我建议。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主持人:这里面似乎暗含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因势利导包含在其中,这是不是有点像打太极拳的感觉?
傅佩荣:确实是,道家基本的原则是柔弱胜刚强。领导者,属于刚强、阳刚,那我就是阴柔,我是你的下属,我当然顺着你,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但是我的阴柔可以让阳刚不要太冲、太直,稍微调和、调节一下。所以道家的思想像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可以调和成为一个整体。
主持人:有人说,历史上那些下场不太好的忠臣,原因是他们不懂得变通,因为他们太刚强、刚烈了,他们要去劝说那些君王,往往是用错误的行为硬碰硬,可是你要知道,君王不认为他自己错,反而以为他自己是对的。这样硬碰硬的话,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如果照刚才那种说法,是不是与一个难以沟通和难以扭转的上级相处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润物细无声?
傅佩荣:对。事实上很多人也认为,儒家好像是硬碰硬的,其实不然,在《论语》里面,孔子称赞他的朋友蘧伯玉说,这个人是个君子,国家上轨道,他出来做官;国家不上轨道,他可以“卷而怀之”,把自己藏起来。孔子也对颜渊说过,有人用我们,就出来做官;没有人用我们,就藏起来,只有我跟你颜渊两个人做得到。正因为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才会说,只有他跟颜渊做得到。这种说法与庄子的原则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由此可知,我们要学会判断时事,你连时事都不能判断,硬碰硬,身家性命就没有了。做坏事的人还是照样做,那你怎么办呢?
主持人:有这么个故事,您能不能从中给我们分析出点什么来?大家也听听,是这样的:有一个总经理,他在某一文件上签了字,就让秘书寄出去。结果秘书偷偷地把它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老板这一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就开始抱怨,不该那么早下决定签下那个文件。这时秘书嘿嘿一笑,说,文件还没有发呢?总经理表面上感谢他给自己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是要给他记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傅佩荣:在于他自作聪明,并且没有给老板留面子。在一个团队里面,有时候要求按照身份、角色承担责任。如果说你不是这一级别的,私自越权处理某事,第一次这样做是对,那以后你每次都这样做,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除非这个秘书自己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上级的一个命令。
主持人:这里面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替他的上级作决策,他剥夺了上级的决策权,是不是问题在这儿?
傅佩荣:没错,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忍的话,那以后每一个层次的人都可以越权处理公司事务,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虽然最后或许结果很好,万一不好怎么办呢?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上面的那个董事长的考虑,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主持人:通过刚才那个故事,我们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变成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做主,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那么,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大家的工作理念不同,连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姜子牙也曾经遇到过和周文王意见不同的时候,他是怎么解决的?
傅佩荣:在《庄子》的介绍里,他根本就不说话,当然,这不一定符合史实了。据庄子的说法,周文王要起来革命,姜子牙不太赞成,他私下认为革命的时机不成熟,这时革命会造成天下纷扰不安,而对于结果如何处置,也没有把握。但是,他没有当面反驳,不说赞成,也不说不赞成,只是半夜一个人就走掉了。走掉之后,周文王才发现,这是对他的说法的抗议,于是文王赶紧自我检讨,连夜追回姜子牙。这也是一种解决上下级不同意见的方法,就是“和则来,不和则去”。
主持人:另外,在上下级之间还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理念不同时,往往会出现矛盾,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所想的实在是让上级没有办法理解,该怎么办?
傅佩荣:在《庄子》里面也谈到类似的故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姜子牙与周文王。周文王想请姜子牙为相,他知道大臣们会反对,因为从外面找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人当宰相,那大臣们怎么看呢?所以周文王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父亲告诉我,要用某某人,你们觉得怎么样?大臣们说,既然是先王托梦,当然照做。周文王借先人托梦之说,就把姜子牙请来为相。姜太公采取的是什么都不做,而什么都做好了,有点像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在庄子笔下,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什么都不做的,“无为”,但是治得很好,就是说,尽量不刻意做什么事,最后反而使得天下可以安定。后来周文王起来革命,把商纣王给革掉。姜子牙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天下已经这么乱了。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周文王就知道姜子牙有意见,不太赞成。可见,庄子讲历史故事,是自己选材加以渲染,达到自己所需要的版本。
主持人:我们刚才讲的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上级该如何来管理下级。现在一说管理,就是什么MBA、MPA,如果庄子来给MBA们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傅佩荣:如果让庄子来教,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成语“朝三暮四”。现在用“朝三暮四”是批评一个人没有常性,说的话又不算数,意见改来改去。庄子的原意不一样,他说,有一个养猴子的人,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有钱了,以后的食物要控制一下,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晚上吃四升栗子。猴子们都很生气,这个人就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早上给你们吃四升栗子,晚上吃三升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听了都很高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猴子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是等于七。庄子的用意是,从整体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那你为什么有情绪呢?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因为情绪困扰对工作的伤害最大。很多人一闹情绪,惰性和抗性就来了,不办公、不做事。因此,领导者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时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可以作为参考。
主持人:现在朝三暮四已经被人以讹传讹了,变成一个人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的感觉。当然,今天我们把故事的原样给大家讲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这是管理者的艺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成本的总量控制、效率最大化的问题。
傅佩荣:对。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除了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参考之外,也反映了庄子的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就是从整体来看问题。譬如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前面少年得志,后来就不一定是大器晚成了。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你就不会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嚣张,失意的时候不难过;看到别人风光不要羡慕,别人倒霉不要去嘲笑。在庄子思想里,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说,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当一个政治领导或者企业的负责人,一定要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在上位纵观全局,才能处理各种复杂的变化问题。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他的管理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主持人:其实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充分发挥古人的智慧,在欧美流行弹性工作制,说白了,就是“朝三暮四”的活学活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管理者的类型,现在流行把管理者分成五种类型:老虎型——自信心强,竞争力强,有决断力;孔雀型——人际关系能力强,擅长口语表达;考拉型——平易近人、强调和谐;猫头鹰型——铁面无私,明察秋毫;变色龙型——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这五种领导模式,庄子会最赞同哪一种?
傅佩荣:如果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庄子理想的管理者类型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卧虎藏龙代表有自信,对于人生各方面的问题充分理解。他如果来当领导,显然是有老虎这样一种能力的,有自信,力量很强,但是他会“卧虎”,不会让你们觉得受到威胁、有压力。“藏龙”,我们讲变色龙,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好像随机应变没有什么原则,但是庄子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这几年,大家常常提到卧虎藏龙这个词,用来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
主持人: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最好的领导者是把老虎型和变色龙型做一个混合,里面是老虎的身躯,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傅佩荣: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主持人: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傅佩荣:如果说请教道家,可以推溯到老子,老子提到领导的四种类型,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
主持人:这叫“太上不知有之”。
傅佩荣:对,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
主持人:“其次近而誉之”。
傅佩荣:接着,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这四种在老子的分法里面,一般人会喜欢第二种,我喜欢老百姓拥戴我,大家都称赞我,投票都选我。但是老子认为,他这次投票给你,下一次不一定了,他恐怕有不同的需求了。最好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管理他,到最后的结论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老百姓说,我们是自己这样子,并没有人带领我们,我们就过得很平静了。所以,老子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连贯起来用在管理上,就是说,当你要领导人,你不要感觉到,别人在被你领导;你要领导别人,要用别人来推举别人,譬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主持人: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统治和管理,在汉初的时候用得特别多。譬如,汉初三杰之一——萧何去世以后,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朋友问他,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啊?他说,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所以啊,萧相国制定的政策要一百年不变,我等只要尽可能地无为而治。后来文帝和景帝也都用过无为而治的管理办法,再到他们的大臣当中,甚至有叫“卧而治之”的,躺着就可以把天下治理好了。这种所谓的无为而治,在管理当中应该如何借鉴呢?
傅佩荣:这可以说是最上乘的艺术,基本上可以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治国者,他本身有一个最高的原则,原则是要天下太平,如果已经战乱很久了,要休养生息,这时就要能够与民休养,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打仗打下来的,过太平日子,才能够日久天长。所以道家的思想,在没有外患、敌国的时候,运用起来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后面有其他的问题,恐怕又要改变策略了。
主持人:我觉得说这么多,就如何管理的问题,我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傅佩荣:这一点很难去证明了。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蒲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国师。等于当宰相了。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他们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三千年,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了之后,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庄子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现在过了两千多年了,我们再来看庄子那个时代,就是出来做官,能改变国家大局乃至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要别的路可以走。人活在世界上,要常常记得,你就算生在不好的时代,生不逢时,或者自己本身遭遇非常的不理想,你还是有路可以走。道家并不是逃避,而是希望,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时,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去,你才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愿意付出或者这个结果没有把握,那你就不要勉强。庄子不是要我们一定要跟他学,他只是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尤其中年阶段,心情跟他类似的时候,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暂时把这些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里面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逍遥自在的一面。
主持人: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去奋斗,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变得游刃有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