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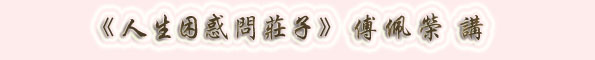
第一讲.庄子何许人也 庄子何许人也
|
|
主持人:有人说,庄子是太空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玄了点?
傅佩荣:确实听起来很玄,但是如果你翻开《庄子》,就可以看到,庄子用三种笔法来描写世界。首先看第一篇《逍遥游》,在《逍遥游》中,鲲变成鹏,鹏一飞,飞到九万里,飞到这么高的地方。庄子说,从地上看天上很美,那么从很高的地方看地上,也很美。而从很高的地方看地上,只有太空人才能做得到。我有时坐飞机听到播音员播报“现在是三万尺高空”,庄子却是在九万里,外太空去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的根据。第二个是在《庄子·秋水篇》里,庄子说,中国这么大,在四海之内,只不过像是仓库里面的一粒米而已。你想想,能把中国看作一粒米,那肯定是在外太空了,太远太远了,整个地球看起来就像一块小小的石头而已。
主持人:这倒是和现在我们所谓的宇宙观很相似,地球再大,在宇宙当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粒子而已。我们就觉得神了,在那个时代,庄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他就像是在太空一样,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傅佩荣:最主要是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中国历代以来,在思想界最令人赞叹的学派。其他各家都跟现实生活不能脱节,并要建立一些生活的规范,找到一条路来走。道家则好像是腾空跳跃,一下子跳到最高的地方去了。
主持人:这么说来,庄子是太空人,听起来确实很玄。
傅佩荣:是啊。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大鹏鸟飞到九万里高,大鹏鸟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回头看什么?看地球。并且说,我们平常在地上看天上,苍苍茫茫真是漂亮,好像很幽远深邃;如果你从高空看地上,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距离产生美感;但是庄子的用意不在于只是美感而已,他希望你能够摆脱现实的各种束缚。另外一段在《秋水篇》里面,庄子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黄河暴涨,暴涨之后,向东慢慢地流过去了,流到海里面去。河伯,就是河神,本来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呢?河的两岸互相看过去,分不出对面是牛还是马,牛跟马这么明显的差异都看不清楚,代表河面实在是太宽广了。但是到了海一看,更加没有边。河伯就说,还是海神厉害。结果海神说,我们都不算什么,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只是仓库里面的一粒米而已。我们想想看,用一粒米来描写中国,那地球不过是一块小石头。
主持人:这就奇怪了,那个时候,一没有飞机,二没有航天飞机、宇宙飞船,庄子怎么就会形成这样的概念?
傅佩荣:因为他是道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道家是最特别的一个学派,其他的学派,譬如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一家都很落实,只有道家例外。他们的落实是落实在具体的生活规范里面,希望找一条路,达到人生的某种幸福、快乐。但是道家认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做了半天是无效的,还不如培养智慧。智慧要靠觉悟,只有一个办法,从“道”来看万物。“道”是代表整体,在整体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值得珍惜。庄子从整体来看时,他才能够超越相对的事物。只有超越高山大海,才能够超越整个地球。譬如说,泰山很高,如果从太阳去看泰山,泰山就很低。这就是庄子的方法。
主持人:今天我们用“庄子是不是一个太空人”作为开头,当然了,庄子不可能是个太空人,那么,庄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傅佩荣: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来看。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对于哲学家不太公平。譬如,他写到庄子的时候,是放在《老子韩非列传》里面,里面插入庄子、申不害。说实在的,庄子蛮委屈的。因为庄子的书里面,解老、喻老,继承老子的是庄子。司马迁也认为《庄子》是老子思想的发展,这一点说得没错;不过他只用一二百字就把庄子打发了。在司马迁笔下只有一句话说庄子说得很对:“其学无所不窥。”就是庄子的学问没有什么书不看的。但是,在提到庄子的著述代表作时,只提到《骈拇》、《马蹄》这些属于《外篇》、《杂篇》的,而没有提到庄子的精华在《内篇》;然后他提出,庄子专门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这些说法其实不见得公平。单从司马迁的《史记》来看,他对庄子的了解有限。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庄子》里面最令人赞叹的是,他把学问了解之后,提升到“道”的高度。他说:古代的人智慧最高了,能够了解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过。即“未始有物”,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过。这一句话让西方的哲学家惊为天人啊,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庄子这种说法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能够发现到宇宙万物根本不存在;我们今天的存在是暂时的、过渡的阶段而已,我们如果从生前死后来看,每一个人也确实不存在。
因此在这个地方就出来一个问题:难道庄子是虚无主义吗?这样一说,我们难免会觉得:那活着干什么?不是假的吗?庄子偏偏就是要化解虚无主义的危机,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很多人自杀,自杀代表虚无主义,活着跟死亡差不多,庄子就在化解这样的问题。可见庄子用心良苦。他本身学问好得不得了,对于一般人他很希望能够给点帮助,那方法只有一个,你设法体验到“究竟真实”,我们是“相对真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百年前没有我们,一百年后也没有我们,那么请问:我们真的在这里存在过吗?今天有录像机,一拍将来可以说好像有,但是你不要忘记,虚拟实景,这恐怕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恐怕都是假的东西,没有这回事儿。庄子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掌握到“道”,相对的万物有“道”作基础,所以不要怕,人生只有一条道可以走,就是设法体现什么叫道。由此,我们才能从庄子这里得到许多人生困惑的一些解答。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虚无主义,也有人理解为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让我们感知的这个世界,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说人生在世,有诸多的困惑,不要说现在很多人最需要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妻子等等一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就是我们自身,也常常会自寻烦恼。您觉得庄子的那种看似比较虚无的、缥缈的哲学,有用吗?
傅佩荣:在现代社会,如果对于现实的各种解决的方案不能满意的话,有很多人就会找心理医生或者各种专家来解惑;但是他们解得让你不满意或者无法从根本上说明问题,那么就只有尝试另外一条路了。譬如儒家。假使儒家让你觉得有压力,那道家说不定可以让你解除压力。其实很多问题,在内不在外,问题不在于别人造成什么环境,而是你自己陷入什么样的盲点,你有执著就看不清真相。可以说,庄子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你要从一种“重外而轻内”的态度转变,变成“重内而轻外”。所谓的“重外而轻内”,一般人都是这样做。你刚才所说的车子、房子、妻子等,正所谓世人所说的“五子登科”,什么都要,但是这些都是“重外”。有的人会以为,得到这些就会快乐;但是问题是,得到这些之后又不见得快乐,说不定更加烦恼。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问:是不是我们过于重视外在的一切?因为外在的东西有时候是没有限制的,像钱是没有人嫌多的,但是多少才算够呢?最后还是要问:多少才算够?你不能一直追逐这个东西,它的范围那么广,有趣的东西那么多,那你如何去求得到呢?因此我们最后还是要把焦点拉到自己的内心里面,让自己先定下来。
主持人:那您就先给我们说说,庄子的哲学,庄子所谓的“道”,能够在哪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傅佩荣:首先,“道”是一个整体,我自己从“道是整体”就得到很多启发。譬如,我这一生是一个整体,我失意、得意的时候,整体加起来的总和是一样的;因此,得意的时候我不会太嚣张,失意的时候我不会太难过。我反而会觉得,一个人要准备好,在失意的时候好好充实自己,调整自己的脚步,将来得意的时候才能走得更久;得意的时候就要珍惜,不要以为现在就胜过别人了,差得远呢,根本就还没有到顶点。如果经常这样想的话,生命会常常保持着一种向上的动力。其次,我学到庄子的“不得已”三个字,“不得已”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勉强、委屈、被迫,而是当各种条件都成熟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我念庄子的书,发现从人的情绪、人心的变化到社会的各种复杂的、黑暗的侧面,庄子全部了解,没有人像庄子一样了解得这么透彻的,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够随时注意到各种人情世故的变化。“不得已”就是说条件成熟,我就顺着去做,所以关键在于判断条件是否成熟;这就需要一种对人间的智慧判断,譬如,我们常常提到,庄子没有做过大官,但是他对于大官的心态,对于大官碰到国君的时候那种紧张、恐惧的心态完全了解。
我们学习《庄子》之后,至少在四个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超越的观点,第一个是空间。我们刚才就提过太空人,平常很多人见面聊家常,一见面就问:你家里有几平方米啊?不要羡慕别人,你再大也只不过在地球上,在中国这一个小小的地方。
主持人:就是在一粒米上面做一个微雕、微刻。
傅佩荣:你说得没错。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梭罗,他写过《瓦尔登湖》那一本书。梭罗一个人住在瓦尔登湖畔两年零两个月,当地很多农夫很好奇,这位哈佛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怎么跑到湖边来住呢?有时候他到农村去买一些工具,别人问他:你一个人住在湖边不觉得寂寞吗?他怎么回答?他表面上说“不会的”,心里想的是庄子的话。他说: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是一个黑点,在黑点上面你问我,我们距离很远,寂寞不寂寞,这不是笑话吗?所以你看,庄子的书能够影响到外国人了。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要化解各种相对的观念,不要羡慕别人地方大,或者有各种设备,不要羡慕这些。
主持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您说大鹏鸟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和作为一个小麻雀,其实也就差不太多,空间上并没有任何的限制。
傅佩荣:对,这一点非常好,为什么呢?这一点正好碰上庄子研究的核心问题。注解《庄子》最有名的是郭象,郭象注解《庄子》有一个败笔,就是你刚才所指出来的:大鹏鸟当然要飞得高,飞得远;我是小麻雀,我本来就在地上跳,这叫各施其性。但是不要忘记,庄子说的是比喻,他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像鱼一样,需要水,不能离开水;但是鱼可以变成鸟,代表人的生命很神秘,很特别,它可以转化。从鱼变成鸟,变成鸟只需要空气,空气对人的限制绝对少于水对鱼的限制;鸟可以飞了,飞到九万里以后,完全不用动了,因为浮力已经够了。所以,庄子是要用这个比喻,说明每一个人都有向上提升、转化的可能,即从身到心、到灵这一层层上升。这是第一个超越,就是相对的空间可以化解。
第二个是时间上。譬如,某某人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而这个孩子夭折了。庄子怎么说,他说,高寿跟夭折根本不需要去分,你再高寿能比一只乌龟活得久吗?
主持人:那当然比不上了。
傅佩荣:是啊,他说,你再高寿能够比得过一棵树木吗?
主持人:那更比不上,树很轻易能活过千年啊。
傅佩荣:你说得没错,所以庄子要我们突破时间的限制。我们也知道,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如果你善用时间,一天就是一年;你如果珍惜时间,人的生命的时间分为客观的时间跟心理上的时间,往往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是永恒一样的。不过,像平常有人说的度日如年,这种说法也不乏存在。庄子突破时间限制,为的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乎时间长跟短。他经常嘲笑彭祖,活了八百岁,又怎么样,还不是结束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的是,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得到觉悟的机会。这是第二个,时间限制的超越。
主持人:那么对第三个限制的超越是什么?
傅佩荣:第三个就是,谈到人在世界上义、利的分辨。“义”就是该做的事,“利”就是利益。
主持人:有的人是舍生取义,有的人是见利忘义。在义、利方面,庄子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傅佩荣:他认为,两者都要超越。我们平常说读书人好像比较高尚,庄子认为不然。他说,一般人去追求利,每天累得要命;读书人求名,每天也累得要命,都不好。甚至,他认为圣人也不好,圣人每天为天下人烦恼。因此,凡是你为身外之物烦恼的,都不好。可见,庄子是这种想法,他说,义、利二者都要超越。否则,你活在世界上,总是会感觉到有所不足;一旦感觉到有所不足,你就有问题了。因为人的生命来自大自然,最后回归于大自然,没有不足的问题;有不足来自偏差的观念,带着偏差的欲望。
主持人:这一点我们今后要好好地跟大家说说,因为很多人的烦恼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第四个限制的突破是什么?
傅佩荣:第四个就更重要了,即突破生死的限制。
主持人:要说到生死,现在每一天都有很多人要面对死神,面对病魔,这都是生死的问题在困扰着大家。庄子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傅佩荣:他的基本的观点是两个字:人活着就好像“弱丧”。“弱”就是身体虚弱的弱,代表年轻的时候;“丧”就是离家出走。庄子居然把我们“现在活着”当作离家出走,那死了呢?叫做回家。这样一想的话,好像死亡没有那么可怕了。
主持人:过去经常会有这种比喻,人死了,说是送什么人回老家,是不是从这儿来的?
傅佩荣:说得没错,我们从《庄子》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古代的成语、格言,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学庄子的话,会觉得有很惊讶的发现。
主持人: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庄子的理念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看起来庄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虚无缥缈,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成指导和帮助。
傅佩荣:是的。但是我们必须去除人们对庄子的两点误解。第一个说他是虚无主义。其实他最实在了,他就是要破解虚无主义,让你找到一个真正实在的“道”。第二个说他是逃避主义,好像是逃避现实,不做官,也不好好赚钱养家,然后说的话往往都是一般人听不懂,跟别人反其道而行。事实上他都不是,他反而是非常正面地去看待生命,只不过比一般人看得透彻。通常我们只看到我们要看的部分,庄子可以看到我们所不想看的,是一个事实的全部分,也就是从整体来看。所以,在《庄子》里面可以得到人生困惑的各种启发。我们不敢说,一定可以解决现代人的一切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的焦点,有时转个弯,说不定就可以想通了。
主持人:可见,庄子显然不是一个太空人,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傅佩荣:前面提过,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庄子不太公平,他是位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哲学家恐怕有一些成见,他把庄子放在老子、韩非中间,司马迁写的《老子韩非列传》有很长,庄子和申不害的篇幅很短,他只用一百多字来写庄子。
主持人:那么在这有限的一百多字当中,他是如何表达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傅佩荣:他说对的是一句话,我们上面也提过,就是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庄子如此博学,几乎是通晓各家各派。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是宋国蒙人,那时是战国时代中期,他见过梁惠王,所以跟孟子的时代是接近的。他做过漆园吏,漆园就是古时候的漆树园子,漆是专门用来作粘剂的。漆园吏算是一个小公务员,庄子大概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好,为五斗米折腰,还是自己去织草鞋为生算了。他一生都不太得意,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既不富也不贵,反而是属于“贫贱”阶层。他的书写得多,司马迁说他写了十几万字,但是现在留下来的不到八万字,被删掉了很多。但是司马迁最令人可惜的是,他举出像《骈拇》、《马蹄》、《胠箧》这几篇,是出自《庄子》的《外篇》和《杂篇》,而重要的《内篇》却绝口不提,我们讲的《逍遥游》,是很精彩的,就是出自《内篇》第一篇。司马迁还说庄子专门批判孔子代表的儒家,以及墨家的一些思想。这些对于庄子的评判,跟我们所看到的庄子的著述有一点落差。
关于庄子的出生地,说他是蒙人,就这个“蒙”字,现在有很多的争议,现在总共有五个地方在争是庄子的老家,即安徽的蒙城,河南的民权县,山东的灌县、东明县和曹县。当然,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愿意争做名人故里,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到底是哪里人,恐怕也很难说得清楚。
主持人:我倒有一个妄想,是不是因为庄子批评孔子批评得太多了,经常把孔子拉到自己的文章当中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说的那些话,可能正是被庄子所利用,来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司马迁不太喜欢庄子,给他写这么一点点的文章。说白了,就是司马迁可能更喜欢儒家,而不太喜欢庄子,是不是这样?
傅佩荣:这个也有可能,不过庄子的材料太多了,可以说是各种想法都有。如果你没有很用心地去看的话,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一旦用心完整地看完之后,就会发现,他有少数几个地方会特别强调,强调要消解各种执著,尤其人间相对的规范。讲到相对的规范,儒家当然是挂头牌了,专门教人各种礼仪;墨家也教人要“兼爱、非攻”这些。那么庄子认为说,你们提出很多理想很好,但是这种理想到了后代变成一种枷锁,绑在我们的身上,让你动弹不得,要求你遵照某种形式跟教条来做,反而失去了人的真诚的心意,庄子他是在这一方面批判得非常的严厉。
主持人: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写庄子就用这么一点点的笔墨,是不是因为司马迁更加偏向于儒家,而庄子的文章看上去显得似乎和儒家有一点点的对立,既然对立,我司马迁喜欢儒家,那我自然要少给你庄子写点,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傅佩荣:对,你说的也有可能。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儒家传授《易经》的传统里面,他是当时的代表,他们司马家等于是孔子的学生传《易经》一路下来的。另一方面,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够把善恶的报应这些都设法写出来。他写到庄子时,会觉得,被庄子一搅和,什么善恶报应都变得很模糊了,甚至变成没有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看,庄子常常用孔子作为他书中的角色,庄子也承认,他说他喜欢用三种笔法,第一个叫寓言,像大鹏鸟,这就是寓言;第二种叫做重言,借重古人的话,要借重古人的话,说出来一定要让别人都知道是谁,那么孔子最适合了。
主持人:那当然,经常打着孔老夫子的旗号,那叫“古人云”、“子曰”或者“夫子曰”,那招牌很厉害的。
傅佩荣:对。第三种叫做卮言,卮就是漏斗一样的,随需应变,庄子是用三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他也承认自己说的话,都是随意说说,不要在意。因为道家有个特色,如果你掌握到整体的智慧,就跟后来的禅宗一样,随说随扫,说完了之后,就扫掉了,你不要执著。就好比是开玩笑,但里面有深意。
主持人:懂得不懂得就看你自己了。我想就庄子和儒家之间这个矛盾,提一个想法。儒家叫孔孟之道,道家叫老庄之道,老子和孔子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春秋时期,而且孔子是曾经见过老子的,向他去问礼,而且见过他之后,几天说不出话来。到了庄子的时候,另外一位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们也基本上在同一个时代——战国时代,比老子、孔子他们晚了大概二百年,那么庄子和孟子属同一个时代,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见过面呢?
傅佩荣:显然没有。
主持人:没有?
傅佩荣:《孟子》的第一篇就是《梁惠王篇》,孟子见梁惠王;在《庄子》里面提到,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做过梁惠王的宰相,等于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住的地方也隔不远。但是古代媒体不发达,两个人恐怕没有办法互相沟通。因为儒家有一个原则,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孔子的话,所以孟子对于像庄子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要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想要为国君所用,来造福百姓;但庄子是一个人笑傲山林,然后自己过苦日子,毫不在乎,跟孟子可以说是,没有见到面,见到面恐怕也没有话说。
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是,孟子不一定想去见庄子,没有这个欲望,但是我在想,庄子是不是也不太想去见孟子?因为在他的笔端,好像常常嘲笑、挖苦儒者,譬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儒者盗墓”,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后来成语“诗礼发冢”的出处,是记在《庄子·外物》当中的,这个故事您一定也很了解。
傅佩荣:是的,你所说的“诗礼发冢”,“诗”是《诗经》,“礼”是《礼记》,“发冢”,就是挖掘坟墓。这个故事当然是庄子自己编的,非常挖苦。他说,大儒生在上面,“有事弟子服其劳”,小儒生就去底下挖了。大儒生问说,太阳快出来了,到底挖得怎么样了?小儒生在里面说,衣裳、裙子还没有拉下来,口中还含着一颗珠子。大儒生说,青青的麦穗长在山坡上,活着不知道做好事,死了之后,嘴巴含珠子干什么(原文: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你要记得,拉他的头发,压住他的下巴,慢慢地用铁锤把他撬开,不要伤害到口中的珠子。你看,在这个时候还引用《诗经》来一唱一和,然后做的是那种勾当,庄子这个挖苦,可以说是到极点了。
主持人:庄子对儒家的意见,要是被同时代的孟子听说的话,那不气吗?
傅佩荣:你说得没错。在《孟子》里面有一段话,他提到墨家代表人物墨翟和杨朱。一般人会把杨朱的做法“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有点像“我一个人隐居起来过我的日子”),跟庄子相提并论,有的甚至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我们现在无法证明。但是孟子批评墨翟,说他“兼爱”,叫做不要父母亲。譬如,我在车上看到父母亲和同样年纪的老人家,我要让座给谁呢?墨家的说法好像是要我的父母亲跟他们猜拳,谁猜赢了,让谁坐,因为我要一视同仁。孟子说,这样的人简直是不要父母亲了,那么杨朱,叫他去拔一毛帮助别人他都不要,他肯定是逃税了,不会去纳税的,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要国家。接着孟子说什么?“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你看,孟子骂得更凶了。
主持人:庄子认为正确的人,孟子就骂得很厉害,我觉得他们这两家学说,似乎真的挺对立的。你看,我们现在表面上来看,儒家要求入世,要求人积极、上进;可是道家呢,给我的感觉似乎是消极、退后。那么,从根本上来讲,您觉得儒家和道家他们是矛盾的吗?
傅佩荣: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学术上的一种研究,我可以讲得比较具体一点,事实上很难具体。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跟道家面对的都是乱世,在乱世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因为做好人没有好报,做坏事又没有恶报,这叫做价值观方面陷入虚无的困境。而儒家专门针对这个。所以我们讲儒家孔孟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自寻烦恼,故意找一些规范来约束别人,不是的。他们强调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善恶的标准,那么善恶的希望,你要行善避恶的希望,只有一个,叫做“由内而发”,每一个人都真诚,我自我要求行善避恶。这是儒家一种很好的理想,他们是希望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给人类重新找到一个价值的规范:真诚由内而发,人性向善。
那么道家则认为,你再怎么教也没有用,因为你一旦把那个善恶的规范列出来之后,叫做礼约,马上变成约束,变成形式,变成教条了,很多人就开始假仁假义;所以道家就说,我要化解的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所谓的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是说,死的跟活着的、活着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乱世,活着只是受苦,很多人自杀都是因为说,活着受苦何必呢?死了是解脱。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的问题。老庄的思想是要解决当时最深刻的问题,让你活着时,不要只想到死亡,因为人最后会死,你不要急,他让你活着的时候去体会什么叫道,要从道的角度来欣赏你的生命。所以道家强调从真实到美感,儒家强调善,真善美就分成两个范围了。儒家强调向善、择善、至善;道家强调从真实到美感。《庄子》一书强调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就可以把前面所说的对立,所谓严重的冲突,稍微化解一下。
主持人:您把真、善、美这样去拆开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我们国人的心中,这似乎是一种审美标准,也是我们的一个行动标准?确实,一个在儒家,两个在道家,那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面都缺不了这两个学说的?
傅佩荣:对,你说得没错。譬如说,我们使用的成语,从小就经常影响我们。从小我们都知道,要奋发上进,讲教育叫启发式教学,让一个人可以不断地在社会上发展,要把个人的成就跟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当然是儒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知足常乐”,道家很多话也变成我们很多日常语言,并以之为警示。所以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血液里面,等于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就有儒道这两个方面的学说成分。
我这几年的研究,我更喜欢把它分成生命的阶段。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最好学儒家,为什么?从学校读书开始都是儒家那一套,进入了社会之后,你要发展个人,成家立业。你要积极进取,奋发上进,当然是儒家。但是到了四十岁以后,你要学道家,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上工作一段时候之后,发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努力的人不一定有成功,做坏事的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报应;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不能灰心,要学道家,学了道家之后就知道,人的生命阶段是一个整体,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成败,而有太多情绪反应。那么到五十以后呢,就要学一点《易经》了。这样一来,就把儒家、道家、《易经》分阶段来不断地学习。
主持人:刚才您用了“化解”这个词,其实听您这么一说之后,就觉得道家和儒家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同,譬如说,儒家讲实,道家讲虚;儒家有很多的规范,道家只有一个道;儒家积极地入世,道家要淡然出世,似乎看起来更加消极一些。似乎有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是不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当中,这两家始终是并存着流淌着?
傅佩荣:对,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常常说,儒家跟道家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儒家是以人为中心,我要给人找到出路,道家是不以人为中心,他不会只对人,他说你不要以自己人为中心,你要以万物为中心,以“道”为中心。譬如说,我们常常说,这棵树有什么用?它结苹果,所以它有用。道家却认为,这棵树何必为了你而结苹果呢?它该结什么就结什么,它不结也是一棵树啊。由此可见,儒家想到任何问题都想到人的需要,是标准的人文主义;道家认为,不要太过于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宇宙万物的价值都被忽略了,所以才说,天地万物都很美,但是,你一说人类需不需要,这个美就被限制为人类的一个需要了,所以道家在这个地方跟儒家可以作为一个互补。
主持人:所以说,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儒家和道家作为我们中国人的两根拐杖,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前行,走到今天,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