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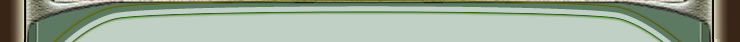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一、 复旦园遇秋雨师
余秋雨先生执教二十多年,足迹遍天下,讲坛也设到了海内外。听过他授课、讲座的人不计其数,就广义而言,他的学生可以数十万计,在当代学人中只怕无人能出其右,堪称桃李满天下。
不过,就学院派对师生关系的严格定义而言,经余秋雨先生一手带出的本科生大约也就数百人,而经他亲手调教出的研究生、博士生就更少了,至今不过十余人。三生有幸,我不仅成为这十几个门生中的一员,还因缘际会,竟做了他的第一届研究生。
其实,在进秋雨师门下之前,我就已经当了他半年学生了。1986年上半年,也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生的最后半年,我所在的8211班开了一门选修课——戏剧美学,任课老师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当时我除了看过话剧《人生》、《天才与疯子》,读过莎士比亚、曹禺、郭沫若的几个剧本外,对戏剧完全是个门外汉,甚至连秋雨先生的大名也没听说过。我对戏剧并无兴趣,而吸引我的选修课又很多,我本来不打算选修戏剧美学的。同寝室的翟宝海同学读过余先生的书,对秋雨师的生花妙笔赞不绝口,极力怂恿我去听他的课。我将信将疑走进教室,吃了一惊,这是间能容百人的大教室,黑压压几乎坐满了人,我的同班同学有八十多人,几乎“倾班而出”都选了戏剧美学这门课,破了我们班选修课的记录。
秋雨师上的第一课就把我给震住了。上课铃响,只见一位个头不高、天庭饱满、腰板笔直的年轻教师健步登上讲坛(后来我知道这一年秋雨师刚好四十岁),他两手空空,未带片纸,只带着一脸亲切而又自信的微笑。复旦四年,我还第一次见到不带讲义就来上课的老师。秋雨师授课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即使你对戏剧一窍不通,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一堂课下来,便彻底把我和我的同学们给征服了。复旦名师云集,我听过几十位老师授课,印象深刻的有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夏仲翼先生的外国文学史,班主任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他们的课有种高堂讲章的学院派凝重森严之感,更多的是给我们以知识的启蒙和理性的思考。秋雨师讲课与他们风格截然不同,他嗓音醇厚浑润,语气抑扬顿挫,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滔滔不绝,以感性的语言化解理论的枯涩,以栩栩如生的描述凸现戏剧大师的风采。他授课看似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其实骨子里有极严谨的逻辑脉络,艺术的感性与学问的理性水乳交融。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如观盛景,是一种陶醉和享受。我在复旦也听过近百名海内外名家如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讲座,不说学问,单以口才而论,秋雨师实为第一人。
当年我求学的复旦大学,弥漫着浓烈的大复旦主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复旦大学”的校徽映衬着每个学子骄傲的脸庞。时常有沪上高校学生来复旦玩,佩带着自己学校的校徽,但很快便承受不了大复旦的傲气,偷偷摘掉了胸前的校徽。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全是复旦的,秋雨先生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为我们讲课的外校老师,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而当时秋雨先生还只是一位讲师,与复旦相比,上海戏剧学院更是一个“弹丸之校”。复旦能请秋雨师来授课,惟一的解释就是慧眼识珠,折服于他的实力。好几年后,秋雨师又到复旦开过一、二次讲座,这时候的他早已名满天下,复旦无人不识君了,远非当年他给我们开课时,走在复旦校园里,识者寥寥的情景了。
听着秋雨师的戏剧美学课,我时常感叹,没能早两年领略到他的讲课风采,没能早两年知晓还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这时候的秋雨师根本不知道坐在下面听课的有我这么一个学生,而我更是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我竟会和他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二、 忝为余门弟子
复旦是个学风自由的校园,给每个学子以极大的选择空间。在复旦四年,我的求学兴趣也一直在变。当时中文系古典文学是显学,我一进校也认为研究古典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于是苦读《文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将来准备考古典文学研究生。读了两年发现自己竟读成了书呆子,一想到将来要和古典打一辈子交道,不禁毛骨悚然,于是开始转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学最时髦,我在最后一学年心血来潮猛啃美学,在同学的一片怀疑目光中考了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生,据说初试成绩进入前三名,蒋先生也有意召至门下。
这时一个偶然原因又破了我的美学梦。我平生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在几位好友中传阅,颇受好评,连陈思和老师也予以鼓励,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搞创作的冲动,美学研究生复试也不去考了,打算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某个报社或杂志社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到了五月份,教育部下达毕业分配名额,我的家乡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来复旦中文系要一个毕业生,去它们那儿教授大学语文。那时候的大学毕业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我那一届复旦中文系只有两名安徽籍学生,我的老乡郜元宝已经考上了文学理论研究生,这个苦差便非我莫属了。我一下子懵了,顿感前途一片黑暗。惶惶不可终日了半个月,突然漫天阴霾中撒下一丝阳光,一份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复试通知书飞到了我的手上。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以陈恭敏院长挂帅,集合了戏剧文学系最精华的老师:陈多、余秋雨、叶长海、丁罗男、汪义群,组成强大的导师组,向全社会招收十名戏剧学研究生,是上戏戏文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生招生。结果没有招满,上戏向沪上各高校进行调剂,让一些落选而又成绩比较好的外校文科考生来上戏复试,于是,我也阴差阳错被选上了。直觉告诉我,这是我逃避可怕的毕业分配的最后一次机会,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离复试只有两个星期,我虽听了秋雨师三个月的戏剧美学课,但我明白我连浩瀚的戏剧海洋的一点皮毛
也没摸到,如何去应试?一向羞涩的我也壮起胆子,趁课间休息时间向秋雨师自报家门,算是与秋雨师平生第一次认识。我向他求教如何复试?秋雨师爽快地回答:这次上戏招戏剧学研究生,强调考生的文史哲综合知识积累,以求戏剧和大文化的杂交,对你们这些综合类大学的考生不苛求戏剧的基本知识。他还鼓励我:你的同学夏岚这次考我们的研究生,考分最高。上戏对复旦学生的素质是很欣赏的。
我从校图书馆借来秋雨师的大著《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戏剧审美心理学》,囫囵吞枣、没日没夜地苦读了十来天,然后横穿上海市,来到小巧玲珑的上戏校园,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先笔试,后口试,笔试主要是看完迪伦马特的名剧《物理学家》演出录相后写一篇剧评,自我感觉写得还可以。口试时我是第四个进考场的,一间不大的教室,六、七位老师在条桌后威严地坐了一排,我孤零零一人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椅子上,颇有受审讯之感。我第一次领教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坐在中间的秋雨师和蔼地笑了:这儿这么多人,你大概就认识我一个吧?我一下子坦然了许多,调动起我的全部所学所得,回答诸位老师的各种考问。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秋雨师,每位老师都向我发问过。秋雨师没有提问,一直微笑着看我,从他脸上我能看到一种鼓励和隐隐的欣赏。我前面的考生口试没有超过一刻钟的,而我足足被口试了半个多小时。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后,我感觉到我有戏了。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小饭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冰啤酒,美美地犒劳了自己一顿。
一个星期后,秋雨师高兴地告诉我:复试成绩出来了,你的笔试和口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上戏的录取通知书。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机,而我得陇望蜀,盘算着既然进了上戏,那就一定要跟一位名导师,而这位导师非秋雨师莫属。
上戏戏文系86届研究生招生和教学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实验:研究生进校时先不分导师,第一年由导师组集体授课,第二年由学生报名、老师筛选,经过双向选择后,再确定由每位导师各带一、二名研究生。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在导师之间和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弄不好会产生矛盾的。但好在导师组的各位导师都是谦谦君子,彼此之间绝无争夺学生之举,他们把这一届的研究生都当作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无论谁好,都为之高兴,无论谁差,都为之惋惜。而我们这一届共十个同学,尽管来自天南海北,彼此之间年龄、爱好也相差很大,但都情同手足,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一起游玩,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绝无明争暗斗之事发生。
一年后选导师,大家根据各自的求学方向、对各位导师的了解和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似乎也都达成了默契,导师组六位导师,每人都有一、二名学生报名,没有出现两个以上学生争报一位导师的现象,也就避免了落选的尴尬。陈恭敏院长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还表示他以前带的研究生都出了国,我跟他自然是有出国机会。尽管我对陈院长十分敬重,但因为当初一进上戏就抱定了要跟秋雨师的念头,所以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分导师时,报秋雨师名下的就两人:曹路生和我。水到渠成地我俩也就成了秋雨师的研究生,而且竟做了他在研究生上的开山弟子。曹路生年长我一轮,自然成了我的大师兄。他本来就是上戏的老师,与秋雨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忠厚好人。后来曹师兄去了纽约大学,师从戏剧大家谢克纳教授攻读戏剧人类学博士,现在又衣锦还乡,继续执教于母校。
我是个虔诚信命之人。没有报考上戏,竟然进了上戏;对戏剧本来不感兴趣、一窍不通,到最后竟然读了戏剧学研究生;对秋雨先生本来是可望不可及,到最后竟然走到了他的身边。对这一切奇遇,我只能理解为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至今我还深深感谢命运的垂顾,让我忝为秋雨师门下弟子!
三、 我亲眼目睹秋雨师的崛起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1986年余秋雨先生带研究生时,他其实还是一名讲师。但这时他又早已经有三部戏剧理论著作和大量文章问世,在戏剧界元老眼里,他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后起之秀,而在大量戏剧实践家心目中,他已是中国头号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更是所有学生最崇拜的老师。论实力他早就应该是教授了,起码也该是个副教授吧?为什么竟然还是讲师?我没好意思问秋雨师这个问题。后来我揣度,以秋雨师的自负和成就,他大概不屑于循规蹈矩,走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条所有高校老师所必走的老路吧?
1987年2月7日,我应复旦同学王满国之邀,在他编辑的《宁波日报》上写了篇千字文,标题是“大家风范——记甬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这篇文章我至今还没给秋雨师看过。下面摘引两段: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系统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
研究戏剧美的具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新鲜度。”
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有时,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我没有查过,不知这篇不成熟的小文是不是对秋雨师最早的评价?
天道酬勤,该来的终于来了。1987年,秋雨师当选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家”,并由讲师一举直升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年轻的教授。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这便是秋雨师的风格。也是在这一年,秋雨师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在书尾他注了一笔:完成于1986年,时四十初度。就这淡淡的一笔,却让我看出了他一丝踌躇满志的心绪。
在我看来,秋雨师从事戏剧学著述,出道不过五、六年,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登上了这一领域在当时中国的顶峰。许多皓首穷经一辈子的白发戏剧学者,影响却远不及这位后起之秀。对于戏剧,该写的他都写了,该说的他都说了,环顾芸芸戏剧学术界,已无人可以在同一层次上与其对话交锋,他大概有了一种寂寞高手的萧瑟之感。然而他的学术生涯才起步不久,他的岁数还那么年轻,他雄厚的文化积累和丰沛的生命力需要有新的渠道得以发泄,新的领域得以证明。当时我就感到戏剧的天地对秋雨师来说显得太小了!果然,秋雨师一转眼就冲出戏剧界,大步踏进更广阔的艺术理论领域,挥就一部《艺术创造工程》。作为理论著作,这部书的文字之美为我所仅见,也许只有蒋和森先生论《红楼梦》一书在文采上勉强可与之一比。看了《艺术创造工程》,你也许就不会惊讶几年后秋雨师能潇潇洒洒地写出那么多美丽的散文了。据我所知,这部书在艺术实践界的反响要远大于学术界,不止一位作家对我说过这本书写得太漂亮了!我一直奇怪,这部深得艺术三昧的书为何至今没有再版?
大概是在1990年,我听说秋雨师正在从事《中国艺术史》这一浩大工程,这更印证了我原来的判断,秋雨师将从此挥别戏剧界,驰骋于新的天地了。但我做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秋雨师不动声色地在《收获》上推出了《文化苦旅》专栏连载,我刚看了一、二篇,就像在复旦第一次听秋雨师讲课,一下子被震住了,而且是更深的震撼。以我在他身边三年,我竟觉得秋雨师一下子陌生了,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直令我感到深不可测。
从《文化苦旅》开始,秋雨师从圈内走到圈外,从国内走到国外,在万众瞩目中走出了一位文化大家。至今我在书店里还经常看到,摆着秋雨师著作的专柜前人头攒动,不停地有人问营业员哪儿可以买到余秋雨的散文。因为秋雨师的出现,一向徘徊在文学边缘的当代散文迅速成了文学显贵。有时候,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真的能大大提升一门文艺种类的品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散文的读者人数论,无人能望秋雨师项背。套用一句“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金庸的小说”,我要说:“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余秋雨的散文”。
四、来龙与去脉
我是个唯天才论者。我想到了今天,没有人敢怀疑秋雨师是一位天才了。而天才往往是不可言说的,要破解天才的成功奥秘,就像解释上帝造物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秋雨师一个不成材的弟子,要对恩师的成功秘密说三道四,恐怕也是贻笑大方。
不能不感谢造物主对秋雨师的钟爱,他在少年时代的超常天赋就展露无遗。他中学时上语文课,学的课文竟然是自己的作文。考大学时听说上戏最难考,要百里挑一,好胜心促使他跃跃一试,竟轻而易举就进了上戏校门。在班上他年龄最小,却公认才华最出众,深得老师喜爱。九十年代中我曾听到一个传言:一位相学大师为秋雨师看相,预言他年过五十后有精神失常的危险,因为他太聪明了,智力太超常了。这个传言我没有向秋雨师求证过,在这儿姑妄听之,姑妄写之。可以说,与生俱来的天才禀赋是秋雨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没有天才,一个人再努力,到顶了也就是一个专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家和大师,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定数!
秋雨师是戏剧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几所戏剧高校里从事戏剧教学的老师,基本上都安于戏剧本行,最多也就涉猎兄弟艺术门类如电影和美术,他们往往是一辈子就一个专业。像秋雨师这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于这么多学科门类、这么广文化领域,集理论家与实践家于一身的,独此一家;即使在当代高校文科里的教授学者,也很难找到第二人;涉猎如此广泛而成就又如此辉煌,更是绝无仅有。我时常惊讶,区区上戏,却孕育了这么一位吞吐天地般的人物!我估计还在学子时代,秋雨师的兴趣就远远超越了戏剧,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就已经打下了雄厚的文史哲综合基础。功夫在诗外,这样当他从事戏剧研究时,就不是简单地就戏剧论戏剧,而是调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积累,牛刀宰小鸡,戏剧难题自然迎刃而解,学术成果自然后来居上。而当他后来转型从事大文化散文创作时,因为有这么广博的文化积淀,他轻而易举地便进入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创造天地。
秋雨师也是幸运的。像他这一辈五十多岁的学人,在文革十年最应该年轻有为的时候,基本上都遭遇了漫长的知识断档和巨大的文化断层,文革后再重操旧业往往是从头学起。秋雨师却以奇特的人生轨迹逃过了这一同代人的宿命。文革前期他奉命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写鲁迅传自然要研究鲁迅,而批判鲁迅的对立面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雨堂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得熟悉所批判对象,得大量研究他们的著述。于是秋雨师阴差阳错地读了大量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人学者的等身著作,日积月累,“批判者
”反而不可避免地被批判对象潜移默化了。在那个荒诞而饥渴的年代里,二十多岁的秋雨师不知不觉地被这些现代大师暗暗滋养着、同化着,酝酿了他充沛的元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这些现代大师被解禁重新成为时髦热点,许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读他们的书,秋雨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对他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了,他一出笔,便隐隐可见这些大师早年落在他身上的烙印。故而在我看来,秋雨师这段被某些人不断诟病、不停曲解的短暂历史,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因祸得福。文革后期,秋雨师看破红尘,退而独善其身,躲进中国古典文化天地里,饱览经书典籍,叩问前贤圣哲,不经意间又打下了扎档墓Ц住S辛苏馐甑男蘖叮镉晔σ怀錾阶匀徊煌蚕欤嬉饧甘直阍对冻搅送恕0耸甏矶喽凉镉晔χ鞯娜耍家晕髡咂鹇胧歉鑫濉⒘甑难д撸奔奖救耍痪铮喊。饷茨昵幔浚
跟秋雨师求学的三年,我发现他是位与时俱进、对国内最新学术思潮特别敏感又特别关注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秋雨师一直对他相当关注,后来还和他成为了朋友。秋雨师看人的目光是极准的,我个人感觉,李泽厚先生不但在当时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没有一位当代中国学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总体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师嘱咐我:有本书你一定要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刚好在这之前拜读过,我暗暗惊讶秋雨师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么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秋雨师对《拯救与逍遥》大加赞赏,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讲了一段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对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秋雨师恐怕是大陆学人中最早一批关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的胡适、林语堂一脉传统,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发扬光大,秋雨师有早年对这一脉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觉得他的天性更与这一脉心心相印,他骨子里是位自由主义者),对海外华人学者自然有惺惺相惜的亲切感。在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无疑大大开阔了秋雨师的眼界,使他思考问题的基点一下子就超越了国内学者拘泥于本土的种种意识形态局限,有了一种全球感和全人类的视野。秋雨师后来在海外获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和知音,不是偶然的。
秋雨师虽然没留过洋,却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独有心得。这首先得益于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万言的《戏剧理论史稿》。西方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大家辈出,许多戏剧家诸如莎士比亚、雨果更是跨时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对戏剧多有论述。要梳理一部戏剧理论发展史,势必要对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因此秋雨师埋首写作《戏剧理论史稿》的数年,实际上是研究、参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朝圣,书写完了,他对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后,秋雨师遍游世界,指点诸国,随手写下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在我看来,他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的多年感悟与心得,最多在书中才写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还深不可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嚣尘上,秋雨师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身为中国学人,无论你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热爱还是憎恨,你都必须去了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于它去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学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是宿命,因为世界学术界不需要仅仅是贩卖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为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文化大师,高者是学贯中西,低者也起码是国学大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垫底,任何人都难以修成正果。秋雨师在他这一辈学人和文人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当属罕见。仅以他的书法论,就越来越见晋唐风骨。在他潇洒飘逸的现代名士外表下,内里却暗伏着魏晋风度和唐宋风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脉,正在秋雨师身上延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秋雨师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超一流的艺术感觉。除了天赋异秉,应该说母校上戏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觉,而长期与第一线的艺术实践密切接触与参与,更是锤炼出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理论家和批评家要让实践家折服是极困难的,而秋雨师的理论和批评却为一大批一流的艺术实践家引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师跟我说他要给一批朋友还债,于是相继给徐晓钟、林兆华、黄佐临、胡伟民、魏明伦等一流戏剧家写了一批专论,每人一、二万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批评文章。魏明伦得到一篇《魏明伦的意义》,如获至宝,从此成为秋雨师的至交。像谢晋、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师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师应该出一本艺术评论集,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评风采。
当代中国学人中,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创性上超过秋雨师的不乏人在,但在对艺术本体的感悟、对众多文艺门类的鉴赏和判断上、在审美感知力和美学品位上,能与秋雨师超凡艺术感觉比肩的,我尚未见到。我甚至认为,艺术感觉正是秋雨师的看家法宝,它使他的学问摆脱了枯涩乏味,具有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悦;它使他的文字表现力在现代汉语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独成一家“秋雨体”,其他人想学也无从学起。天才与艺术感觉珠联璧合,让秋雨师笑傲天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锦绣文章,秋雨师潇洒地做到了。
五、愧对师门
能进秋雨师这样一代名师的门下,对任何一个学子都是莫大的幸运。我的许多复旦同学见我做了秋雨师的弟子,也都羡慕不已。当年我进上戏时才22岁,先前在复旦苦读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点底子。进上戏不久,叶长海先生就帮我推荐发表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可谓年少气盛。导师组不少老师都觉得我底子不错,是可造之材。秋雨师能将我纳入门下,显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说有秋雨师这样的高人指点,只要我潜心向学,刻苦研读,是会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然而当年的我年轻无知,胸无大志,又生性懒惰,意志薄弱,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只要资料馆要你的学生,我这儿没问题。就这样,秋雨师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在秋雨师带过的几届研究生中,可以说我的毕业分配是最让他费神的了。而我当时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师把我的找工作也当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秋雨师曾感慨地对我说:继高啊,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也没这样帮忙过呀!
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混了几年,凭兴致所至杂七杂八的事干了不少,却毫无成就感。有时候在社会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绍我: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总能引来几道爱屋及乌的
目光,而我却有无地自容之感。都说名师出高徒,可我实在是不配称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实在是有辱师门。
过了30岁,我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再朝秦暮楚、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而且也实在对不住所出师门。于是我决心专攻一门,从1995年开始正儿八经写起影视剧本来,又在1997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捧起了电影这一没落贵族的饭碗。这几年影视剧倒是写了几个,能勉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择》和《走出凯旋门》,混了个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编剧,算是在圈子里初步立住了脚。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不了秋雨师的高徒,今后的岁月里我只能尽量努力,不至于再给师门抹黑。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