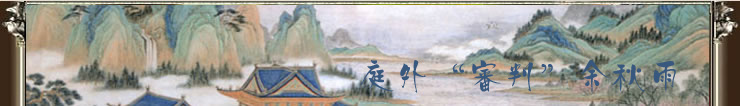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看余秋雨告状左柏生:正版中的盗版(1)
|
 |
 |
|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牵涉到了有名的余秋雨先生。但我总是对此欲语又止地打不起精神,生怕啰里啰嗦的太麻烦。
然而最近无意中打开报章,却读到了这般热闹非凡的消息:
7月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收到了一张特快专递送达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作为文坛焦点人物的原告余秋雨,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十万元、经济损失六万元。一个是著名学者、作家,一个是知名台港文学专家,这一事件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冲击着并不平静的当下文坛。(见2002年8月1日《中华读书报》)
更有甚者,这篇报道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担任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的余秋雨24日下午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的主要观点由马兰代为转达:最近有一系列的官司,不仅仅是起诉古远清一个人。这不是余秋雨和古远清的单独对仗,也绝不是文艺批评过度的问题。余秋雨今年将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牵涉的不止一个城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上)
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那么看起来曝光率很高的余先生就早已是打定主意不怕麻烦了。既然如此,我也索性打起精神凑凑热闹,把自己以前的发现讲给读者听听?当然这也许只能聊博大家一粲,因为对于这等上不了台面的事体,恐怕并不需要调动起“名誉”啦“侵权”啦之类的严肃字眼。
先得读一段1999年作家版的《霜冷长河》,当年这本书曾因为跟盗版图书的种种搏斗,获得过非常热门的广告效应。
余秋雨先生在这本书中写道: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第140页)
光看余秋雨先生的字面,那当然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不仅如此,围绕着“谣言”这个话题,他居然还显得那样博雅和规范,既从善如流地引用和肯定了刘东先生的观点,还进一步援引了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看法,对本土学者的观点小事补正,从总体上显得更加全面、平衡和充实。我想绝大多数善良的读者,都是会这样来理解上述文字的。
可是,真是不比照不知道:天下的“学问”竟还有这样做的?
以下我们照录刘东先生的原文:
那么,讲了一圈,究竟如何总结对谣传的透视呢?我们先说一下卡普费雷先生自己的定义。他认为,人民称之为谣传的东西,必须同时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第一,该信息必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第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第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54页)总而言之一句话--谣传是照某一类人听来既出乎意料又恰在情理中的“路透社”新闻。
这定义固然不错,但还嫌不完备,因为它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下的。而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审查,则我们还可以对之进行重要的补充--谣言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这正是我想要说的“谣传的悖论”,或曰“谣传的怪圈”。(《谣言的悖论》,《浮世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3-124页)
破绽昭然若揭!原来,第一,其实人家刘东先生的那篇文章,本来就是从述评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传播学著作——《谣言》入手的。第二,不过刘东先生的旨趣,却又不止于引述别人想法,而希望围绕谣言问题进行再引申,去揭示一种悖反的认识论怪圈。第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首先原原本本地列举出法国学者对谣言所下的全部三个定义,然后再尝试着下出自己的(第四个)定义,以便从各个角度把此中的规律补充得更加完备。
一篇文章写到这里,在没有发现新的道理之前,本来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惜,经过余秋雨先生无事生非的颠倒顺序,整个事情也就被颠倒了味道!尽管乍读起来,余秋雨先生也很尊重别人的创造,但只要把两个文本搁在一起,就可以无可辩驳地发现--其实他此处所耍的障眼法不过是:先从一段文气非常完整的文字中,把人家原本提出的第四个定义挪到前面,然后再回过头去,从人家的引文中单独摘出一组定义中的第二个。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戏法,刘东先生那番本意去补充别人的定义,就反过来被颠倒和歪曲成了视野褊狭、读书不多、有待补充的思想素材,等着余秋雨先生去舞弄文墨发挥新意了!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