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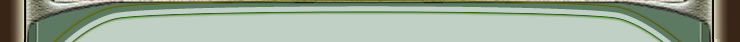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在此书快要写完的时候,忽然读到《南方周末》发表的《文化人的沉沦》(何家栋),开头云: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创举。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
余秋雨在《我的法律行动已经圆满结束》的声明中把告肖夏林败诉妄想为“胜诉”,肖夏林为此感到“又未免大煞风景”,因而“动用惩罚手段”称余秋雨为“文坛首骗”、“文化恐怖分子”。我不赞成这种“惩罚”和给别人乱戴帽子的做法。
余秋雨喜欢给别人开书单,在这里,我也不妨建议余秋雨读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关于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不能“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马克思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 为了保护“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马克思是如此大义凛然地谴责“最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希望文化界的朋友为了保护弱者“述说真理的权利”,不要惧怕余秋雨的淫威,昂首挺胸起来遏制余秋雨这种文化“恐怖”活动及其秋雨横飞、寒气袭人的“恐怖”文风。如不遏制,中国文坛必无宁日,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学术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何家栋进一步指出:
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和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击只等闲”,都没有对簿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有“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一些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马克思说“批评即审判”,如果将“审判变批评”,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
只要有这种文化品位,就不会有阿Q式的解嘲和纯属自欺欺人“圆满结束”的说法。事实上,余秋雨打的三场“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的官司,从勉强胜诉到和解到最后败诉,呈极明显的大滑坡趋势。
余秋雨“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的官司之所以不是“圆满结束”,是因为他声称要打十多个连环官司,可现在只打了三个就把刚摆出的拳击架势收了回去。他扬言官司要“打五年十年”,可只打了一年多就收摊。他多次扬言下一个要告的目标是孙光萱。可孙氏既是原余秋雨写作组的“同事”,后又成为写作班文艺组党小组副组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余秋雨感到告他有如烫手的山芋。如果告这位给余秋雨所谓“造成了几乎一生的灾难”的孙光萱,难免有翻清查案之嫌。因这触及到如何评价中共上海市委70年代末清查“四人帮”余党工作的成绩,乃至当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及后来清查其余党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类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相信法院难于或者说根本不会受理此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在法庭上就曾明确告诉原告:“文革”中作了结论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余秋雨在2002年8月底答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问中,装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说把“刑事案件”降低为“民事案件”是对我的优待。这正说明他欠缺法学常识,因这原本来属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根本不沾边。
余秋雨告肖夏林一审败诉后,以第一时间写好《上诉书》,攻击北京东城区法院“既说了错话又做了错判”,东城区法院许多“可笑的概念,将被人们牢记”,可终审败诉后又改变腔调“感谢法院对我的洗雪和抬爱”,这不是有点言不由衷么?他如此善变,和他在“文革”中由保守派一下腾飞为“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何其相似乃尔!
余秋雨是中国文坛最善于吹牛的作家。他在新加坡大言不惭地说: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建立法治意识”,可这回他告我以和解而非胜诉告终,告肖夏林则一败再败,这是不是说中国法治就没有希望了?再加上上海《咬文嚼字》资深编辑金文明及其他众多学者一齐“咬嚼”余秋雨,使余秋雨浓油重彩涂的“文化昆仑”的面具被卸下。他连告都不敢告也无法告金文明,说什么“他的问题是经济炒作,并没有损害我的名誉,不必起诉”。这“不必起诉”是“无法起诉”的意思。金文明虽然没有损害他的名誉,可金文明挑错的书《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在台湾再版后,余秋雨的台版书《文化苦旅》由每月销售一千册降为三百册左右,这损失真是惨重。他不想起诉金文明是假的,只是这纯属学术问题,无从下手罢了。这就难怪余秋雨在接受台港媒体采访时装出一付可怜相,说“也想过不再写作,甚至离开中国”;还以“文革”时受迫害的老作家老舍相比:“那时候,许多人只能靠自杀来维持名声,他们是最弱的一群。”他在境外以廉价的眼泪骗取台港读者的同情,在内地则以霸气十足的劲头告媒体告学者告作家,真可谓是恶人先告状。他在内地与境外的言论判若两人,这也许就是他讲的人格分裂吧。他还说什么金文明等人都得到官方支持,由此可看出他说谎及色厉内荏的本质。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