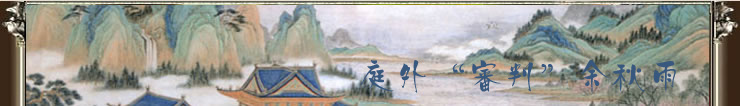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海内外来信选登(2)
|
 |
 |
|
我很快要进入古稀之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见怪不怪也,即以秋雨“文革”所作所为,年纪大的上海文化人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公道自在人心,你不必多虑。即使上海法院不主持正义(他们敢吗?),判你输了,也不要紧,那时你可登报声明,并搞个募捐运动,凑不到十六万,凑一千六百元总可以吧?真的你输了,估计也就这个数,这样反而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
我当然不希望你做失败的英雄,但在上海打这场官司,你得小心为妙。如果判你败诉,就有可能说明上海司法欠公正,或上海高层仍有“四人帮”的势力或受帮派思想影响的干部,这对上海形象更为不利。
不过,奉劝你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如赵忠祥告一位小记者报道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卖皮鞋一事失实,从而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赵凭着他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地位和身价轻易获胜,可这场官司赢了又能证明什么呢?只不过证明没有售书搭皮鞋,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同样,余秋雨如果胜诉,法院判决的也只不过是余秋雨没有写过批“斯坦尼”文章,可他写过一系列的大批判文章,这只不过是减少一篇而已,何足补哉!
你要找朱永嘉,他不便也不会说的,除非法院找他当证人。我有时看到他或散步或买菜。他正在专心从事古籍注释工作,算是与专业对了口,有人将他做的工作比之为好似老和尚念经,完全是修心养身之道。但他毕竟还未看破红尘,有时也会发点牢骚,如谈到那位“一号种子选手”余某人时,他曾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现在不也很红么!”
前天见到“任犊”写作组的一位成员,他提供了一些新的“任犊”文章系余某人所写的线索,你可找他聊聊,或许有新的收获。
祝你大捷!
也有的原写作组成员对我研究“余秋雨现象”颇不以为然,认为“你完全是圈外人,何必凑热闹”。下面是这位先生写的长信摘录:
远清同志:
信及文,均悉。谢谢!祝新年好。
……看来,你和肖夏林都怒气未消,还要穷追猛打。我奉劝一句:和为贵。我已渐渐看淡了远去的刀光剑影,当时闹得挺凶,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不必过于认真,大体明白就可以收兵了。中庸之道,是讲究一个度,超过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凡遇纠纷,也要适可而止,不要往死里整。……
望多保重身体,少动肝火。
平安、健康就是福。
这封信语重心长,值得我参考。尤其是“和为贵”的建议很好,我后来之所以愿意放弃有胜诉的可能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就是本着“大体明白就可以收兵”的原则。但不是我把对方“往死里整”,而是他把我“往死里整”。我只不过以“文革”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考证余秋雨在“文革”中用过什么笔名和写过什么大批判文章,对其作个案解剖,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其中还对他说过不少肯定和赞扬的话,并批评了余杰、朱大可过于极端的说法,可他只取我说他“狡猾”这一点,把我告上法庭,扬言要我“倾家荡产”乃至“进监狱”,可见不是我跟他过不去,而是他大动肝火,一个劲地把我“往死里整”。我取“中庸之道”和他握手言和后,他仍“怒气未消”,重弹我“造谣”和“诽谤”他的老调,这就使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真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缘由缘由。其目的是告诉后人,余秋雨当年“闹得挺凶”的打连环官司一事,“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这时期还有不少好心的上海朋友劝我“和为贵”。如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开会时,一位该校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跟我说:“老古,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大院,他有后台,你搞不过他的,和解算了。”
我听了后顿生疑惑:“文革”中余秋雨是康平路写作组本部的大红人,里面有他的房间和用来讨论大批判文章的办公室,想不到现在他又重返康平路(但不是住在大院),他真是什么时代都吃得开的人物。但我就不信邪,他有后台难道法院就不主持公道了?
另一位复旦大学教授说:“原‘石一歌’写作组副组长吴教授你认识,他也是余秋雨的好友,干脆请吴教授做鲁仲连,把你们的矛盾化解算了。”
我不想求人,特别是不想找多年未联系的吴教授,以免打扰他,另方面我觉得这位朋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此外,我还接到不少上海的来信,其中也有一位上海某大学教授劝我“调解为上”:
古兄:您好!
寄上我们与曹文轩教授的合影,光彩太暗,只能算个意思吧!
您与余秋雨先生的事,容我多一句嘴,还是调解为上。毕竟“文革”时,秋雨先生还年轻,不懂事。再说,他当时也不是有意伤害人。他成名后,有人专揪住他这条小辫子,他十分恼火,亦属情有可原。不必揪得太紧。能恕则恕,孔子的恕道还是大有深意。当然,这次是他主动挑事,但我们下笔还是应该宽缓为上。
本人学出复旦,但与余秋雨先生确无任何关系。上述意见纯属一个局外人的个人看法。我会关注这件事的发展动态的。
祝顺利!
此封信说余秋雨当年“不懂事”,这未免小视了能担负起江青、姚文元、朱永嘉委以重任参与批判“斯坦尼”工作的余秋雨。说人们不该“专揪住他这条小辫子”,现在的问题是他不承认自己有“小辫子”。至于说“能恕则恕”,我完全赞成。我之所以在上海没有反诉余秋雨,告他捏造全世界都没有的《南方论坛》来加害于我,就是本着这个信条。现在的问题是他不对我“恕”,要把我“绳之以法”。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