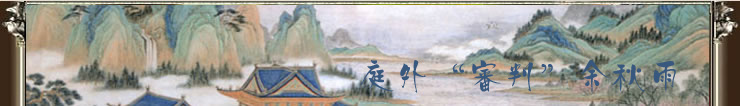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咬文嚼字的“调解方案”(2)
|
 |
 |
|
又是把全案归结为“斯坦尼”。起诉书上告我诬蔑余秋雨“狡猾”,“诬赖原告于1969年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说我发表“蔑视法律的言论”,说我“捏造”他写过《戏剧美学》一书,还有什么“人命案件”,以及要我在八种媒体上刊登“赔礼道歉”启事,这回统统都不提了,或曰“撤诉”了。
基于对方这种出于无奈的让步,我向法院表达下列意见:
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人愿意对有关文章中史料有不准确之处,向有关媒体作出更正,并表示歉意。
二、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三、更正的内容应围绕起诉书中讲的“1969年”参与写作《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此文的发表“给她(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这两点。如果是这样,那《文学自由谈》、《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涉及到这两点,因而只能在三篇文章中进行更正。更正时只能用学术更正的方式写,共分三种:
(一)本人在《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文艺报》2000年3月21日)中,称余秋雨先生在“1969年”参与写作《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红旗》1969年第6、7期)一文,与事实有出入,特予更正,并表示歉意。古远清 2003年6月30日
(二)本人在《余秋雨与“石一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中,称余秋雨先生在“1969年”参与写作《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红旗》1969年第6、7期)一文,与事实有出入,特予更正,并表示歉意。 古远清 2003年6月30日
(三)本人在《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中,称余秋雨参与撰写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发表“给她(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与事实有出入,特予更正,并表示歉意。 古远清 2003年6月30日
第一、二个启事“称余秋雨先生在‘1969年’参与写作”,理应完整地写成“余秋雨本是1968年参与写作,我误为1969年”。但既然是和解,也就不这样写了。第三个更正本来也应写作“给她(孙维世)致命打击”应改为“给周信芳、贺绿汀、瞿白音、郑雪来等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命打击”,但为了给对方留面子,此启事还是愈朦胧愈好。
从原告方的《调解内容》与我的《更正启事》相对比,不难发现双方最大的分歧是:余秋雨认为自己没有写过评“斯坦尼”一文,我认为参与写作过,这点绝对不能否定,我的差错只是原告参加大批判组时间和孙维世之死时间分别误差一年。
我向庭长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原告不是没有参与写,而是1969年没有继续参与写。应明确肯定:原告1968年参加了。他说的五篇文章(实际上是四篇)只有三篇涉及两种年代的误差问题,应按起诉书要求更正。而鲍培伦坚持余秋雨没有写过那篇文章。后来我不想再与他争下去,本着邓小平讲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笼统地说我的文章关于原告参与评“斯坦尼”一文“部分内容有出入。”
在分别调解时,原告希望用严重一些的词句,但其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故只能做些小动作,如把“有出入”改为“与事实不符”之类。“部分内容”的提法估计余秋雨接受不了,王茜灵机一动就说改为“相关内容”,我也同意,这位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书记员便立刻高兴地到对面的房间告知正在与原告沟通的许伟基,后又由原告方把“相关内容”改为“有关内容。”
许伟基问我这种改法同不同意?我想,“有出入”与“与事实不符” 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至于“相关内容”与“有关内容”有什么不同,只有天晓得。这种无聊的文字游戏再玩下去实在浪费时间,我想:既然对方不再认为我侵权,就在词语上让他一步吧。
过了一会,两位法官很快起草了《调解协议书》。关于第一条“表示歉意”的提法,原告曾表示要按起诉书上说的“赔礼道歉”或“表示道歉”,法院则希望原告按被告《更正启事》中的“歉意”一词,他只好表示同意。
2003年3月我在上海开会时,曾征求过上海作协一位资深评论家、原为“丁学雷”成员有关对原告可不可以“表示歉意”的意见,她说:“余秋雨是后来参加写作组的,我的资格比他老。但我很快被赶了出来。”又说:“只要不是向原告有无参加写作组和撰写大批判文章一事表示歉意,就可以。单纯的史料错误问题向对方表示歉意,是很正常的学术说明,不要多虑了。” 《文艺报》负责人也在座。他十分赞赏孙光萱《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写得恳切和实事求是,认为只在评“斯坦尼”一文的年代误差而不是有无参与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表示歉意”,这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体现了和解的诚意。
至于是笼统地“表示歉意”还是“向原告表示歉意”,我当时有过踌躇,但我想既然是和解,还是出现“原告”这一主语好,鲍律师听了后说:“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对他这种反应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不是有意把陷阱给他跳,但这样一来,打官司又成了考语文常识了。难怪许伟基先生在最后通过《调解协议书》时说:“我们这是在咬文嚼字”。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