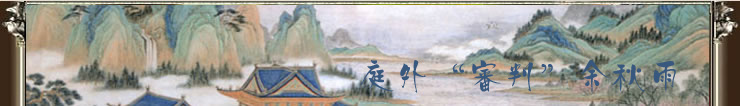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周培松挺身而出
|
 |
 |
|
在上海除有夏其言这样主持正义的文化人外,另有一位同样挺身而出的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周培松。
周培松(1932- ),江苏南京人,1949年12月参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时,荣立三等功一次。1958年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戏剧理论与戏剧教学工作,除创作、改编四部大型戏曲剧本上演外,并发表戏剧理论及报告文学、剧评、散文等四十余万字,出版有论文集《戏剧的倾斜与制衡》,并写有回忆录《神州一觉五十春》。
周培松于1979年奉上级指示,和别的干部一起补查原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的“文革”问题。1979年上半年,夏其言在市委办公厅召集部分单位开会,把上海市清查工作中群众意见颇大或没有完全查清的“说清楚”对象放到本单位进一步复查,其中上海戏剧学院分到的有余秋雨一人。周出席了那次会议,会后并将内容向上级作了汇报。
我在2003年8月17日晚到上海徐家汇访问了周培松,我们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龙井茶,一边翻阅《戏剧的倾斜与制衡》自序,其中云:“我过去认为、至今还认为,‘文革’十年即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太奇特,太值得回味了。例如,那时发表了什么大批判一类文章,许多人就由不得的像那待宰杀的牲口一般露出惊骇的眼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人们面前出现的那把流淌着血水的快刀就是笔杆子功能一种精致的转换。尔后,笔杆子们借着那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花翎顶戴,同时臆造出种种精妙绝伦的理论,使人心安理得地对待这种处境,又文质彬彬地完成了第二种转换。如此这般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没遇上实在是一件幸事。不过对笔杆子的功能,则少了一层感性的认识,当然也不会触及这个过时的、颠倒迷乱的故事了。话说回来,今后倘若有这个营垒的人物或做法卷土重来,那么年轻人在思辨的突破上倒是可能获得对比观照的乐趣,不无裨益。”想不到,周培松的话竟不幸而言中:而今,当年“笔杆子营垒的人物”余秋雨“卷土重来”,用打所谓连环官司的“小文革”方式翻清查的案,这引起了周培松的严重关切,因而他打开话匣子回忆道:
“余秋雨为什么敢告你?上海戏剧学院有些人议论说,是因为戏剧学院了解余秋雨情况的老人,或去世了,或离退休了。中年人对他有所了解,但还在岗位上,可能有所顾虑。我为什么敢站出来支持你?我曾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枪林弹雨都经历过,‘文革’的味道也耐心地尝过,可谓‘曾经沧海’了,还能不识一点是非与真假吗?我部队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61年毕业。1973年又调回戏剧学院工作。2000年看到《新民周刊》严重失实的报道后,我曾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老人向市委组织部和《新民周刊》反映过余秋雨的问题。余秋雨参与评‘斯坦尼’一文的写作,我记得他当面承认过,这在上海戏剧学院是人人皆知的事。余秋雨当时年纪轻轻,能担负起这一重任,他也以此为荣,现在如果将此否定,那历史不成了可捏可搓的泥人吗?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余秋雨今天为什么要变卦,而是要弄清余秋雨今天为什么能如此‘入戏’?即使有人看中他那几本书,难道文品与人品就没联系吗?其中会不会有深层的原因呢?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为犯的是一般政治错误。在复查中,有人对这一结论有不同看法,觉得定得偏低。后来大家认为不要以单一结论看人,而应以事实看人,找出人物的历史轨迹,这样就比较符合实际了。后来我们就查事实,并未对原结论提出看法。即使这样,他后来当戏剧学院院长,院内外仍有不少人反对,但大概考虑到当时人才缺乏,加之干部体制原因,便当上了。”
与周培松会晤后,他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退休教师(曾任系总支书记、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参加过院、系“清查”工作。在此过程听人说过,余秋雨“文革”早期参与了批判“斯坦尼”文章与资料的编写。而对此言论,我并未听有人表示异议。
特此说明。
周培松 2003年8月
这里对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一事极为肯定,并提供了他还参与言论摘编的工作,而这个“摘编”我后来已当做证据之一提供给法院。周培松这个证词虽然在对簿公堂时来不及出示,但已足够说明我说余参加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写作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知情人进行广泛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上海戏剧学院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且是清查他的人而非一般的教师。周培松的证词和夏其言的抗议信一样,有很大的权威性。余想通过打官司翻清查的案,看来还真不容易呢。这次只在上海戏剧学院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余来说就是后院起火,用余的话来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周培松对余“文革”中的表现还有许多事来不及谈。当时夜深了,我只得告辞回到华东师范大学。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