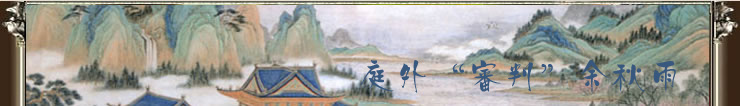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脱光衣服显丑”
|
 |
 |
|
被网罗进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成员,现在多数人都不愿意提这段伤心史,其中一些人为自己当年盲从动乱年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后悔。社会上也有些人不能正确对待他们,把他们误上贼船比做抗日时期落水的汉奸文人,骂他们是“无耻之徒”。其实,这些写作组成员多数人品行并不坏,业务能力也很强,不让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作贡献,是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的。像原历史组成员、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就曾被打入冷宫多年,应有的学术待遇在较长时期内得不到解决。余秋雨比陈旭麓就幸运多了,因他当年参加写作组刚大学毕业,所做的事都在社会上而不在上海戏剧学院院内,因而“民愤”不大,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贡献较顺利地当上了院长。
写作组的成员自清查后,各奔东西。其中有少数人成了激进文化路线的牺牲品,大多数人改正错误后,为人民再立新功。在他们中间,有的当了大学校长或文学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图书馆馆长、专业报负责人、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更多的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叙旧,在节假日有时聚会。余秋雨自然是大伙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均为他在学术上、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对他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颇为不满。
在上海搜寻证据的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接触过原写作班文艺组、哲学组、历史组的一些成员,其中意外地得到一份在原“市委写作组与秋雨共过事的朋友”写的一首题为《谦虚与恐惧》的新诗,开头云:秋雨经过“文革”后的等待与努力,加上他的才华,已成为文化名人。但他却因此否认与“写作班”的任何关系,致引起他与余杰等人的争论。读《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秋雨作《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有所感,作此诗。
一
多么豪迈的语言,
“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朋友,对你的豪言壮语,
我感到脸红。
算懂得历史的“文化名人”,
你不惜抹杀历史,
犯下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
二
什么叫“得意忘形”?
华丽而狂妄的语言,
为它作了详尽的注释。
辩证法让人走向反面。
三
历史可以反思,应该总结,
却容不得篡改,更不能抹杀。
“名人”光圈纵然炫目,
却掩饰不了真实。
乔装打扮,
等于脱光衣服显丑。
四
时代不能选择,
命运有福有祸。
有英年早逝的王守稼(1),
也有再度红得发紫的余秋雨。
天上人间,祸福相倚。
不能因为腾云驾雾,
就忘却神州大地曾秋风秋雨!
五
忏悔不必,掩饰是巧伪。
历史的碑石,
毁不掉,敲不碎。
在人世沧桑中怀有良知的人,
来不得半点虚伪。
“面对历史真实,
我应当怀有永恒的恐惧!”
2000·7·24作
(1)王守稼,复旦大学毕业,也是写作组成员,“文革”后因脑瘤逝世,终年四十七岁。
作者并非中文系出身,想不到他能将知性与抒情结合得这么好。诗中对当年写作组的秋雨朋友“乔装打扮,等于脱光衣服显丑”的表现,尤其是对秋雨“华丽而狂妄的语言”所作的尖刻嘲讽,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为“再度红得发紫”的余秋雨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作了生动的注脚,是一份比证据还要有说服力量的材料。其中“历史的碑石,毁不掉,敲不碎”是格言式的警句,对那些“面对历史事实”“怀有永恒恐惧”的人,读了此诗尤其是了解到作者的真实身份后,也许真的会产生“恐惧”感吧?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