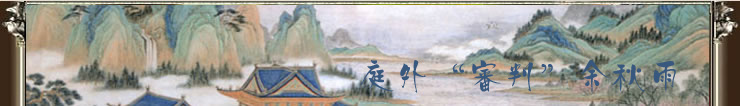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略施小计(1)
|
 |
 |
|
我虽然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但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好在我有不少学生都在本校法律系任教,楼上楼下也有法学院教授,因而我连忙向他们请教,可不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他们都表示赞同,因而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变更管辖法院的申请书》:
申请人:古远清,男,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竹苑小区××栋×门×××室
对方当事人:余秋雨,男,住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弄×号×室
请求事项:变更管辖法院,将本案移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事实与理由:
原告余秋雨认为本人侵害其名誉权,于2002年6月25日向贵院提起诉讼。本人认为应由武汉法院审理此案。理由如下:
1.被告住所地在武汉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人认为应当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也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从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可以看到,余秋雨所引述本人的文章发表媒体均是北京的《文艺报》和《鲁迅研究月刊》、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合肥的《学术界》、南宁的《南方文坛》。所谓“侵害名誉权”的文章,没有一篇在上海发表。至于他在“诉讼请求”中提到的《湖南日报》,简直匪夷所思,因本人从未向《湖南日报》投过稿。上海《新民周刊》也从未发表过我的文章。故本人声明,“侵害名誉权”行为地不在上海。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认为此案应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利于查清本案案情,有利于被告人参加诉讼。恳请贵院将本案移送管辖地。
此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古远清
2002年7月17日
我动起打管辖权异议这张牌,使法院不能于8月27日顺利开庭,是无师自通——不,是受了《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天岛、南芭编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这本书的启发。“马桥”诉讼——即小说家韩少功因其著作《马桥词典》受到北大张教授等人的激烈批评而将对方告上法庭,被告便从提管辖异议开始“玩”这场“法律游戏”(顺便说一句,读者诸公以后如遇到此类案件,也可以如法炮制)。有人告诉我,要求更换法院得到批准可能性不大,但不妨一试。法院对此案受理得这么快,余秋雨又想速战速赢,以便开打他一系列的所谓连环官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正好缠住他、拖住他。
我这一略施小计的行动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并引起一些海外人士的议论,如美国的政论家曹长青在《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文章中写到:
现正进行的原中共厅级官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诽谤案就是这样,因古远清撰文指出余秋雨曾是“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写作成员。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要由被告古远清“举证”余秋雨“文革”中怎样以文整人,而不是由原告余秋雨举证他没有这么做。古远清明明是引用余秋雨在上海的“文革”战友已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但余秋雨不告那个上海作者,反而来告古远清;而且不是在古远清所居住的武汉打官司(按中国法律应在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硬是不按规矩地在原告余秋雨居住的上海打。这样就逼迫古远清一次次从武汉跑到上海。对于一个穷学者来说,不仅路费、精力、体力难以吃得消,而且要他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余秋雨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对方认输,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他人不得对“余院长”等党的文化官员说三道四,进行监督批评。曾被当局考虑提拔为文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余秋雨说,要对批评他的人和媒体逐个告,“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这段话突出了余秋雨的政治身份,说明他告我是想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压人。曹长青还说我“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这是因为当事人均怕牵连自己而不愿轻易开口。文中最后一句所引余秋雨的话倒使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文革七、八年要再来一次。”余秋雨这次以“恶攻”、“炮打”之类的“文革”思维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而且扬言官司要五年十年打下去,也许就是“活学活用”这种理论而从事的一种他自己说的“小文革”吧。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秘书长张放先生也在《中央日报》发表长文《隔海评品笔墨官司》,其中云:
这是余秋雨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古远清,姿态摆得过高。余某家住上海,叫被告千里迢迢,从武汉跑到上海打官司,他是很有气派的,但条件未免过分刻薄,且有南霸天的味道,让人不服。
这里用“南霸天”的比喻,余秋雨可能又会认为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其实这不过是给这位号称文化大师的鼻梁上涂了一点白粉,无非是要他不要盛气凌人之类,这也无伤大雅。本来,余秋雨在台湾的版税收入据《苹果日报》公布,高达二千八百万新台币。这样一来台湾读者当然对你余秋雨的“文革”历史有知情权和评论权。此评论权先不说“文革”往事,就说你在台湾拿了这么高的版税,你到底交了多少税金?金文明跟你指出这么多常识性错误,你再版时一字不改,能对得起台湾读者吗?这些总该给台湾读者一个交代吧。否则,台湾读者和评论家又会出现比“南霸天”更难听的说法,那你就得从此岸告到彼岸而告不胜告了。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