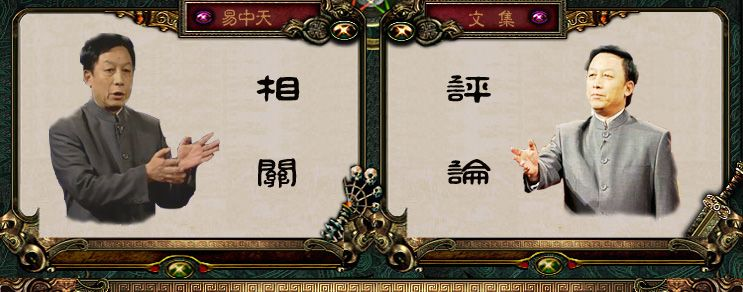 |
|
“明星学者”易中天
|
 |
|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走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后家喻户晓,成了“老少通吃”的明星学者。前几天,易中天来上海,记者在他下榻的衡山饭店等候。易教授戴着墨镜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如大明星的做派。我们开玩笑说,好像没有哪个学者需要戴墨镜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吧?他一边摘下墨镜,一边无奈地说:“我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
确实,易教授的上海行在上海也刮起了不小的“易旋风”。他在上海书城为“品读中国书系”签名售书时,整整4小时,签名签到手酸。场面火爆令人叹为观止。第二天他在上海图书馆作题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读三国及其他》,老少书迷把报告厅挤得无插足之地。最后,易教授还让出了自己的主讲人座位,站着给大家上了精彩的一课。此举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在广大读者心中,无疑又加了不少分。
稀里糊涂当了明星,不自由
问: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
易:不好,不自由。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前几天在厦门和太太一起去看电影《南极大冒险》,怕引起麻烦还特意挑选了早场。谁知道,电影院里一共才八个人,四个人就把我认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会收到电子邮件、帖子还有来信、电话等等。我确实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已经不接电话、不看信、不看邮件、不上网,这些工作只好交给我太太去做。我回家以后就把手机交出来,由她代接加重了她很多的负担,但是我实在忙不过来。
问:您觉得一个学者被明星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易:就个人来说,你看你需要什么利。坦率地说成为这样一个人物的话,钱肯定是多了,借钱的人也多了(笑),弄不好还被贼惦记了。但是就生活而言,真的是弊大于利,因为你不得安宁了。其实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喜欢过安安静静的生活,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哪怕这个书房不大。但是四周放着都是自己喜欢的书,很温馨、闲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以后喝自己喜欢的茶,写一点东西,这是我们这类人最愿意过的生活。
问:当时答应中央电视台上“百家讲坛”主讲是基于什么考虑?
易:也没什么考虑就稀里糊涂答应了。我这人不看电视不上网,但是“百家讲坛”我是知道的,就是借助电视媒介讲学术话题。我觉得,第一,电视对我来说不陌生,以前我在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做过谈话节目;第二,对讲坛我也不陌生的,只是换了个“课堂”而已。我就说,行啊。不过第一次上电视讲的时候还是没有经验,感觉比较模糊。第一讲是《曹操之死》。后来就好了。
《品三国》竞标,是首创
问:为什么要采取竞标的方式来给《品三国》书稿找出版社?这在全国出版界好像还是第一次。
易:是啊。“品三国”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很多出版社都表达了希望能出版这部书的愿望。据初步统计,表达过意向的出版社有35家左右。我感到有压力,这其中有老朋友,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就是他们出的。也有新朋友,香港三联、东方书局都是很好的出版社。想来想去,干脆还是招标吧,大家公平竞争。
问:这样操作会不会有炒作嫌疑?
易:当时我们出于综合考虑。应该说,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所以,我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决定联合作为招标主体,挑一个强势出版社,强强联合,实现三赢局面,创造新闻出版和文化产业的新模式。之所以采取招标形式来选择出版社,还是希望把书做好。既然打算走向市场,就要按市场的形式运作,彻底市场化,公平竞争,这样公平、公正、公开?
问:那事先你们有没有定标?整个招标工作怎么进行?
易:我们是无标的竞标,不设门槛,面向全国有意向的出版社。竞标定于5月22日下午两点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到场的出版社可以参加竞标,可以只观摩不竞标,也可以当场决定竞不竞标。我觉得将来畅销书就是走这条路。整个竞标主要是三项数字:版税、初版印数和保底销售数。由北京市公证处全程公证,当场唱标。
问:这些项目先看什么后看什么?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怎么办?
易:这三个项目应该是有考虑先后次序的,这个我没得到授权不能说。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最后由竞标委员会定夺。
问:您心里有底价吗?如果低于市面上的行情怎么办?
易:没有底价。如果招标的结果低于行情,我们也接受。
问:您的书稿都要竞标挑选出版社,而有的老专家一辈子埋头研究,到头来连出本书都难,这公平吗?
易:什么叫公平?我觉得很公平。很多专家学者,他的著作本来就是给圈内同行看的,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我本来就是服务大众的,虽然我也有写给圈子里的小众看的书,比如《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只印三千册,还有《艺术人类学》。不过,这两部书出来后,我就决定改弦易辙了。你写给小众看,就要付出代价,就是要面对出书难、印数不高的问题。而我现在也是付出代价的,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招骂。
问:您现在这么火,也招来不少不同的意见,您在乎吗?
易:我无所谓在乎不在乎。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要付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不是你自己想象得出来的,而是需要事到临头才去面对。我觉得,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一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我选前者,宁可别人说,不能自己说。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没法掌控。
明年2月28日,退休了
问:走上“百家讲坛”面对全国几亿观众,是不是借强势媒体比较容易出名?
易:无论哪种类型的学者,成名绝非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尽可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让大家共享。学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就要大家分享。电视又是个传播面广的好媒体。不过,“百家讲坛”引起轰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问:您现在很红,有“明星学者”之称,余秋雨先生也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明星,您觉得你们俩走的路一样吗?
易:我不知道余秋雨是不是靠电视走红的。我觉得他出名还是那部《文化苦旅》。他是散文,我是随笔,接受群体虽然有交叉,但还是不一样的。
问:现在您北京、厦门两地飞,还有时间给学生上课吗?
易:上啊,主要带博士生。“品三国”才刚开始,讲多少还不知道。每一集我要准备四五天,每个月要讲四集,这样就二十天了。2007年2月28日,我就从厦门大学退休了。
问:您说,好东西要大家分享,那这对您个人的学术研究是好事还是坏事?
易:我给自己定位: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就是一个探路人,是“扫雷”部队的,随时准备牺牲。我希望能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对接,要让传统的东西被现代人接受;要实现学术和大众的对接,这要有人“以身试法”。电视和学术的对接是有风险的,做得不好,电视失去观众,学术失去了品位。文史哲是人文学科,以人为本,以人的幸福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总有一部分人要直接为当下活着的人服务,我们很多学者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当然,还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问:从“百家讲坛”的走红,是否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做文化普及工作?
易:请注意,我从来没用“普及”这个词,而是“对接”。听众的定位是需要有一定生活阅历和文化的。我没想到会有一大群年轻人喜欢。有年轻人喜欢就是实现了对接。
问:听说喜欢您的读者从8岁到80岁都有?
易:是的,他们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应该是我们本来的追求目标。
问:有没有做过“下课”的准备?如果有一天不红了,您会不会感到失落?
易:我随时准备下课。对我来说,这么“红”非意料中的,就好像天上掉馅饼,本来也没打算有这个“馅饼”,何况我还已经咬了一口,已经赚了。
如果是硬伤,认错好
问:电视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易中天”这个人,您现在还看电视吗?
易:电视还是不看。但我自己节目看的,主要是挑毛病,先挑自己的,再挑编导的。
问:一些人对您引用现代词汇的“说书”式的讲座方法有不同意见,甚至有评论说“误人子弟”和“满嘴跑火车”。面对那么多的批评,您怎么看?
易:我欢迎批评,尤其是欢迎那些充满善意、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批评。现在表达意见的渠道很多,有各种形式,打电话的,有写信的,有向记者发表谈话的,也有在网上发帖子的。一个节目播出来以后,所有的观众都有权利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这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我原则上只对正式的批评作出回应。
问:怎么看待余秋雨在青歌赛点评时读错字的事?
易:我也是听别人说起这事,就专门查了一下。“仁者乐山”的“乐”确实读yao(去声),是喜爱的意思。在美学界普遍把这个字念作le(去声),连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都没有注出来,一些权威的书也是翻译成“快乐”的。这个字太生僻,念错也未必就是大不了的错误。
问:您在电视上出过错吗?怎么处理?
易:我也有,譬如把(juan)城,念成zen城。有观众指出来,我发现确实读错了,特地重新录音,还向他道歉并致谢。对这类问题,我认为不是多大的错误,如果是硬伤,还是认错为好。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