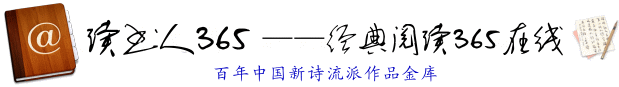
一场静悄悄的诗学革命
--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宏观考察
--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宏观考察
□谭五昌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生前曾经作出过"艺术终将消亡"这一惊世骇俗的预言,给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里热爱艺术的人们投下了心灵的阴影。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黑格尔关于艺术的诅咒式预言在20世纪末中国新诗身上似乎获得了初步的兑现:公众对当代诗歌的兴趣和热情伴随时间的流逝呈"直线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普遍的淡漠和厌倦态度,与刚刚逝去的20世纪80年代诗歌广受人们欢迎的"火爆"景象构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反差。人们仿佛遵循了某种神秘意志目睹着"艺术(诗歌)消亡"时期的到来。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当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现代汉语诗歌在公众中所遭受的普遍冷落,既不是某种神秘意志的"公然显露",更非"艺术消亡"的外部表征,而是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发展的逻辑产物。换言之,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诗歌日益"式微"的命运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转型,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思潮对整个社会成员的精神结构和价值观念均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更新"与"塑造"。其结果,使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成为相当部分社会成员的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和追求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从而导致人们对于高级艺术形式和精神形式--诗歌,产生普遍的疏离感与深刻的隔膜感。这是时代与历史意志的必然凸现,而非神秘意志的突然"显灵"。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共谋"对于当代诗歌在80年代赖以迅猛发展的精英文化(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形成了强力的冲击与消解,给当代诗歌持续、正常的发展态势带来了某种灾难性的负面影响。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诗人们面临这么一种普遍性的困惑:他们发现自己的诗歌写作完全处于"失效"状态。他们"突然"被时代从热闹的中心位置"驱逐"到荒凉的边缘地带,在社会上扮演起了"多余人"的角色。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戏剧性转换使90年代的中国诗人普遍萌生深刻的价值困惑感,甚至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失重"状态。不过,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语诗歌并未在时代非诗性的强大压力面前呈完全的衰颓、消歇之势,反而表现出韧性十足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大思潮(诗潮)在90年代期间的"陆续崛起",并在诗人们当中逐渐获得深入人心的效果:此两大思潮可概括为"个性主义"与"理性主义"。此两种思潮是围绕并针对当今时代精神的总体状况而萌生滋长起来的,它们关乎诗歌写作的伦理道德和价值问题(而非诗歌写作的技术问题),因而极具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个性主义"已与8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个性主义"具有质的区别。在80年代的"朦胧诗"(或"新诗潮")和"第三代诗"(或"后新诗潮")那里,"个性主义"均显现为一种激进的文化姿态,其文化诉求的目标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呈现出浓厚的社会意识色彩,难以摆脱社会情结的纠葛。进入到90年代发展阶段,"个性主义"至今已呈现出独立的人文品质。故而,在时下那一大批仍然坚持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诗人们那里,"个性主义"已成为一种最为根本的写作伦理。"个性主义"成为90年代以来至今所有坚持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诗人们最为可贵、最为鲜明的品质之一,由此还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写作原则与诗学主张:"个人写作"(或"个人化写作")。"个人写作"这一诗学主张为诗人们写作时取材(题材)及主题的"个人化"乃至"私人化"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支持。"个人写作"命题的提出在90年代初期,到当下已成为一种普遍自觉的写作实践。换言之,它已经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写作理念了。"个人写作"所产生的诗歌文本都是以传达诗人们独特的、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其旨归的。这一趋向和特点近几年来在一批坚持"口语写作"或"泛口语写作"的年轻诗人那里表现得颇为鲜明,这是与他们喜欢从现实生活经历中直接提取诗性经验的写作嗜好与写作习惯分不开的。
如果说,"个性主义"为当下的诗歌写作(包括整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独立的精神品质,并为诗人们的写作行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价值保证,那么,"理性主义"则凸现了这批陆续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晚生代"诗人(与崛起于80年代诗坛上的"朦胧派"诗人与"第三代"诗人比较而言)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化态度,具体点说,它既指明一种人生态度也指明一种诗歌态度。从年龄角度而言,我在这里所谓的"晚生代"诗人特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包括少数"第三代"诗人在内),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80年代诗歌潮流及文化思潮的冷眼旁观者或懵然无知者,因而他们的生命(生存)观念只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紧密的关联。在那批"晚生代"诗人那里,"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智、清醒、务实的诗歌态度和人生态度,接近于思想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非指文学理论上的创作方法)的含义。因此,这批"晚生代"诗人在思想意识上普遍排斥在80年代诗坛上颇为盛行的浪漫主义诗歌潮流。相应的,80年代诗歌文本中常见不鲜的青春激情、乌托邦情结及形而上的精神狂想在当下的诗歌文本中几乎已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对时代状况及个人境遇的冷静观察、描述与剖析,对现实的理性悟解已经远远超出诗人自我的情感诉求。不过,从取材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两种路向:一种偏好从中外典籍、名人掌故那里获得间接性的文化经验,以曲折的方式映射社会现实;另一种偏好以自身的日常生活经历作为表现与反思的对象,从中获得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的思想感受。一个来源于书本,一个来源于生活,趣味虽然各异,但理性的求索与呈现却是两者的共通之处。概而言之,"理性主义"是诗人们面对实用主义盛行的当下社会文化语境所保持的一种颇为明智的文化姿态与写作姿态,它在缓解诗人与时代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方面堪称一剂理想的"精神镇痛处方"。
"个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平和文化姿态使得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不可能像20年前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那样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因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奉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激进文化姿态("第三代诗"的叛逆意识可以视作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加之它们正好呼应思想启蒙与个性解放的社会文化思潮,因而往往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社会轰动效应。当下的汉语诗歌却失却了这种文化功能,更准确地说,当今诗人们宏大的文化抱负与这个时代构成了悲剧性的"错位"关系,如此,当下的汉语诗歌被一再"边缘化"乃是其必然的宿命。人们往往习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盛赞20世纪80年代汉语诗歌写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以此作为基本的衡量与评判尺度,对当下乃至整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给予贬抑性的评价,而人们也常常据此对于汉语诗歌的发展前景持极端悲观的态度。
事实上,用这种尺度来评价与看待当下的以及整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状况是非常偏颇且有失公允的。在我看来,情况应该刚好相反:从诗学的角度上看,当下的以及整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充分自觉且高度成熟的建构阶段,在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理论化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突出表现在"晚生代"诗人们诗学见解的丰富性、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与深刻性等方面。比如,在诗歌主张上,"晚生代"诗人先后提出了"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后口语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70后诗歌写作"等诗学命题,并能就这些诗学命题的不同内涵、特征乃至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作出清晰的阐述和学理分析,理论视野开阔,逻辑推断严谨,见解独特、到位,表现出"晚生代"诗人身上不同的诗学建构能力及良好的诗学素养。此外,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诗歌写作传统也依然处于继承、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发展阶段,诗人们的诗学建构及诗学悟解能力整体上尚处于不断探索的状态,诗文本中过多的文化与思想的负荷"遮蔽"了80年代诗人们的诗歌本体意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异常鲜明地凸现其相对纯粹的艺术品质。在商业大潮及各种世俗性诱惑构成的"冲击波"中,作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队伍主力阵容的"晚生代"诗人们,反而获得了一块冷静反思的精神空间,其从事诗歌写作的心态反而也趋于纯粹,他们在不被公众理解的寂寞状态下孜孜追求汉语诗歌的成熟与完善境界。怀着对于诗歌纯粹的喜欢、欣赏与热爱之心,他们尽力帮助诗歌摆脱种种非诗因素的干扰与"遮蔽",使诗歌恢复其纯粹、可爱的"本真面貌"。因而,在"晚生代"诗人那里,"诗之为诗"的意识与理念比以往任何一代诗人都要来得更为强烈与自觉。换言之,"诗歌本体意识"在"晚生代"诗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诗歌的"集体无意识"了。他们通常乐于采用诗话或诗学论文的方式,片断性或系统性地阐述他们对于"本真诗歌"的真诚见解与观点。与当下多元文化的时代语境相对称,"晚生代"诗人们的诗学观念也呈多元化格局,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有些观念构成互补关系,有些观念却构成对立与冲突。这些丰富、歧异的诗学观念源于诗人们不同的写作立场和审美情趣,并未表明诗歌内部的混乱,恰恰是诗歌内部生态平衡的正常反映。其极其难得而可贵之处在于:尽管"晚生代"诗人们的诗学观念由于其多元开放性而看似"混乱无序",但它们都呈现出内在严肃的艺术态度,力图从自身的角度逼近诗歌的本质,将对诗歌的认识与理念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堪称一场真正上的"诗学革命"!
之所以将"晚生代"诗人丰富、多元的诗学见解称为一场"诗学革命",是相对于以往诗人传统的诗学观点而言的。比如,在关于诗歌的叙事性、戏剧化等表现手段,以及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写作等相互关系的理解与阐述上,"晚生代"诗人做出了具有时代高度和哲学深度的全新回答,传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诗学观念,强力地震荡并冲击着因时代变迁而显陈旧的传统诗歌意识。值得指出的是,这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在当下臻于成功的"诗学革命"是以"静悄悄"的姿态出现和进行的,这一方面表现在"晚生代"诗人们很少采用大张旗鼓的方式公开兜售自己的诗学主张,像"第三代诗人"那样取得哗众取宠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表现在"晚生代"诗人们更习惯于通过诗歌文体的精心营构来传达自身独到的诗学观念。
与当前多元文化社会存在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情况相一致,在"晚生代"诗人们当中也根本不存在一种规整而统一的诗学观念。在"晚生代"诗人多元诗学话语并置的"混乱"情景下,从中可以发现诗人们诗学意识上的一个共同"兴奋点":对词语的极端重视与高度关注。可以说,在"晚生代"诗人看来,词语已不仅仅是传统写作观念的上命名工具,它就是命名本身,是一首诗产生诗意的直接来源,对词语的合理选择与使用成为一首诗成败的关键。在此,词语的作用已具有诗歌本体论的非凡意义。"晚生代"诗人对词语普遍持有程度不同的迷恋情绪,甚至萌生"词语情结",这不仅仅是诗歌的语言意识的觉醒,更是诗歌的本体意识的觉醒。在当下,"诗人的痛苦就是语言的痛苦"这种创作经验的表白已经获得诗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且可以视作"语言诗学"建构意向的一份简洁、生动的宣言。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的韩东曾经发表过"诗到语言为止"这种颇具"语言诗学"意味的诗学言论,但韩东的这种诗学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只被人们当成一种纯粹的诗学假设来看待,那时的诗人们尚未从诗学本体建构的意义上给予语言(词语)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第三代"诗歌文本与其诗学理论主张的普遍脱节就是一典型例证。而在当下,诗歌的"语言意识"(或"词语意识")在诗人们的写作观念中已经被内在化了,成为指导诗人们进行诗歌写作的一种普遍性思想原则,或者说,语言意识已转化成诗人们一种强有力的写作动机了。
对于词语(词语是语言在文本意义上的一种称谓)的诗学本体价值的普遍关注使"语言诗学"在"晚生代"诗人那里成为一种理论共识,但"语言诗学"的建构由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的可能性需要相应的写作实践加以推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年长于"晚生代"诗人的王家新和于坚就写出了充满"词语意识"的诗歌文本《词语》和《O档案》,于坚的《O档案》被有的评论家称为"词语集中营",可见该诗歌文本内词语密集的程度,而王家新对自己跨文体写作的诗文本命名为"词语",更具有某种开风气之先的象征意义。这两位诗人后来因诗学观念和写作趣味的局部冲突与对立而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于词语的重视和迷恋却达成了一致性的默契。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状态与前述情况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但情形显得更为复杂,整体的理解与把握也显得更加困难些。因为在以词语为中心所建构的诗意空间里,"晚生代"诗人们关注的焦点决不止于词语的独到搭配与组合,而且凭借词语的通道来承载诗人关乎个体与历史的经验内容以及诗歌文本的形式追求。这种状况必然决定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丰富、复杂的艺术与精神风貌。从对词语的不同选择、使用以及美学趣味与风格追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相似性来看,我们可以对于"晚生代诗人"的当下诗歌写作大致归纳成三种类型或倾向,下面试作简要描述。
写作倾向之一:"书面语写作"
持有"书面语写作"倾向的诗人通常追求语言的典雅气质,注重语言的修辞效果,尤其强调词语的想象力。"书面语写作"这一诗学命题与"知识分子写作"存在一定的重合关系,但后者主要是对写作者身份的一种命名,诗学意义不大,在具体的诗歌写作活动中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持有"书面语写作"倾向的诗人数量众多,这既与汉语诗歌写作传统的深厚积累有关,也与书面语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普遍性的文化经验和人生经验这一"语言功能"关系密切。受诗人自身不同的诗歌趣味与写作追求等个体性差异因素的影响,在坚持"书面语写作"的诗人群体也呈现出风貌上的差别与殊异:西川追求语言表达上的雅致、精确与隐秘的心灵体验合而为一,文化感与生命感在他的诗文本中常呈水乳交融状态;杨晓民则显示出其善于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提炼诗意的敏锐感受能力,诗的语言呈现鲜活、生动且不乏幽默感的品质;西渡善于从日常性的题材发现形而上的主题,同时在对词语进行不露痕迹的打磨与组织方面显示出扎实的艺术功力;臧棣擅长于冷静的理性观察和智性判断,他的诗歌文本结构上的"均衡感"以及富有沉思效果的叙述语调与节奏的能力为许多诗人所欠缺;沈苇常以西部风物取材,但他能够逸出题材上的"地域意识"而使其诗歌的主题朝"历史意识"与"哲理意识"敞开;雁西偏好词语的典雅与庄重色彩,注重诗中情绪的流动与智性的感悟自然地交汇在一起;礼孩诗中简洁、干净的语言节奏运用得娴熟自如,具有极强的情感冲击力。除此之外,李自国追求语言与精神的双重力度,王明韵追求智慧空间的无比开阔,代薇追求词语的优良质地,董晓文追求以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手段获得宏阔、深刻的历史意识,而安琪和道辉则追求词语自由奔涌与组接的"意识流"写作效果......
当然,从典型的意义上来看,持这一写作倾向的诗人们更加普遍注重对词语的想像(联想)力和对事物的相像力,以及这两种想像力的综合平稳状态。在这一点上,张况、程维、桑克、姜涛、蔡天新、哑石、席永君、海男、叶舟、巴音博罗、丛小桦、孙磊、蒋浩、非亚、普珉、唐亚平、吕叶、周瓒、简宁、韩高琦、叶匡政、马永波、刘漫流、何房子、李郁葱、迟宇宙、吴文尚、穆青、曹疏影、徐晨亮、郭文斌、袁毅、朵渔、徐南鹏、徐勇、池凌云、荣荣、阿信、凌迟、韦白、林家柏、禄琴、清平、远人、巫嘎、刘洁岷、彭凯雷、李阳泉、汪剑钊、魏志锋、牛放、兰荪、昌政、牧斯、肖飞、邱勇等诗人均有出色或比较出色的表现。他们的诗歌文本中普遍具有较为浓郁的理性色彩。另一批诗学观念相对比较正统的诗人则依然关注诗的抒情性,在小海、蓝蓝、罗亮、汗漫、刘亚丽、李南、古马、小叶秀子、鲁西西、赵少琳、江熙、潇潇、卢文丽、发星、亢霖、祝凤鸣、梦亦非、李寂荡、侯荣、胡建文、风劲、胡少卿、虫儿、谢夷珊、廖慧、伍迁、黄海、黑黑、孙子·乌子、李贤平、石继丽等诗人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抒情因素在诗歌写作动机及诗歌内容的构成上所具有的重要位置。由此,有力地显示出"书面语写作"在诗学追求上的丰富性及开放性特征。
此外,在"书面语写作"的范畴之内还存在一种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神性写作"或"准神性写作"现象。很明显,"神性写作"是从精神追求的向度上对那些坚持"书面语写作"倾向的诗人的一种集体性命名。从词语选择的角度来看,具有"神性写作"倾向的诗人追求词语的圣洁色彩和崇高意味,极度重视词语象征性的精神价值和内在光芒,甚至萌生一种"圣词"崇拜情结。持"神性写作"倾向的诗人往往具有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化抱负,对世俗价值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但他们在诗歌写作中各具自己的特点:李青松在诗句中处处洋溢的英雄主义的拯世情怀与闲适逍遥的出世态度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境界神奇动人;单永珍用词语建构的神性境界则高远而空旷,充满苍凉悲壮的北方气息;江雪从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出发向神性体验迈进,词语的朴实性与神圣性水融交融;而姚辉、陈先发、王琪、杨建虎、唐朝晖、王冷阳、徐柏坚、白连春等诗人则注重在神性价值的照耀下充分袒露人性的美丽与悲哀,具有净化灵魂的艺术情感效果。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持"神性写作"或"准神性写作"倾向的诗人虽然为数甚少,但他们对于维护人类精神的高贵与尊严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
写作倾向之二:"口语写作"
坚持"口语写作"倾向的诗人强调以日常生活语言和民间语言作为自身的"诗歌语言资源",追求语言的朴素、本真与透明效果,反对与摒斥修辞手段。因此,在"书面语写作"倾向中常见的隐喻、象征、暗示等诗歌表现手法在追求"口语写作"的诗歌文本中几乎被"扫荡殆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口语写作"的诗学主张逐渐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声势与潮流,甚至成为许多青年诗人刻意追求的"写作时尚",这与大众文化思潮的日益泛滥以及与其地位的日益巩固存在紧密的关系。口语化的诗歌文本从语言到精神都完全消解了"正统诗歌"所存在的"贵族化"倾向,以平民或普通人的文化姿态向"大众"的阅读趣味"回归"。需要稍加反映出与提醒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那里,"口语写作"一时也成为潮流,但当时的"口语写作"体现为一种激进的文化姿态(反叛精英文化),而当下的"口语写作"却体现为一部分"晚生代"诗人的一种人生态度(认同社会现实)。据此,有些论者将当下的"口语写作"命名为"后口语写作",以示与前代诗人"口语写作"在精神方向上的区别。
当下"口语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状态。也就是说,许多在理论上主张完全运用口语写作的诗人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也证明或反映出许多主张"口语写作"的诗人追求"诗歌的原创性"的难度所在。不过,具有严肃艺术探索性质的"口语写作"却能在冲破以往那种相对规范的诗歌写作模式中显示出清新的风貌和可喜的活力来。作为"口语写作"理论与实践上的代表人物伊沙,其早期的诗歌写作无论语言姿态还是文化姿态都显得颇为激进与前卫,近期的诗歌写作兴趣却似乎转移到对题材的生活化(日常性)与口语的"本色化"(反修辞)的刻意追求,更加注重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中岛的诗在语言上显得简洁、朴实,但对其内在情感体验的表达和呈现却异常深刻、到位,具有"深度抒情"的动人艺术效果;向隽能将题材的某种形而上性质与语言的日常性品质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具体的叙述中流露机智、反讽、俏皮的精神特征;盛兴追求词语的"透明"效果与诗歌内容的"透明"效果,在对语言和事物本质的非凡感情能力与命名能力上,确实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中显得尤为出众;沈浩波追求语言的极端感性色彩(感官效果),强调身体对于事物直接感受的重要性,但他的诗歌写作仍以对于词语和事物丰富的想像力见长。而其他一批持有"口语写作"倾向的诗人,或追求客观冷漠的"零度写作"(如贾薇、马非),或追求生命的感性体验(如岩鹰、唐欣),或追求写作的"在场"与"现场感"(如吕约、尹丽川),或追求调侃、审丑的"后现代"品质(如野鬼、南人),或追求叙述的朴实和本色(如冉冉、戴华)......如此等等,旨趣各异,构成了"口语写作"极其丰富的内部风貌。
写作倾向之三:"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
从当下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况来考察,这种"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写作倾向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这是"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写作"两种语言写作倾向交融互渗的产物与结果,它既显示了诗歌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显示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诗人们(相对于他们的前辈诗人们而言)更为开放的语言态度与更为突出的诗艺综合创造能力。持这种"复合型"写作倾向的诗人们追求适度的修辞效果,追求自由的艺术空间,他们往往能根据诗意创造的需要而灵活地安排口语与书面语应处的结构位置,从而成功地实现一首诗的创作意图。从阅读效果来看,这种"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倾向既能够保证诗歌创作的庄严与纯正品位,又能有效地维持诗歌创作的生机与活力,堪称一种理想化的诗歌写作范型。
不过,这种"复合型"写作倾向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写作"所具有的一般性特点,在许多诗人身上仍能加入独特的或综合性的创造因素。比如,莫非和秦巴子能把他们笔下的词语赋予唯美与神秘的感性色彩,而主题却能指向高度的形而上境界;李元胜和刘波能够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发现戏剧性因素,并对它们进行充满智慧与幽默感的"喜剧化"处理;郁郁和张执浩处理时代性的主题时,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积累对悲剧性的时代精神加以喜剧性的表达;侯马、徐江、宋晓贤擅长利用自身充满忧伤感的抒情气质对日常生活题材处理得诗意盎然,文本显得精致而优美;谢湘南、刘川、森子、金海曙则沉潜于对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观照,他们的诗歌文本洋溢出与生活本身一样鲜活的智慧感;凸凹、稚夫、余丛、空中楼、张亮则善于将"反讽"的精神因素不露痕迹地渗透到对他人与自我的观察与描述之中。
从诗人个体角度来看,创造性因素同样分明。树才对于词语拥有丰富、活跃的想像(联想)能力,这使得他笔下的事物常常闪现美妙动人的诗性光芒;余怒则在词语的感悟能力与组织表达能力上表现出颇高的艺术天分;路也诗的叙述语调外表平静、节制,但寓含反讽、沉痛的精神内质,极富张力效果;赵丽华对于词语出色的想像力与对于事物的理性把握达到了较为完美的平衡状态;林童的语言姿态朴实无华,但饱含深沉的忧患意识;娜夜的诗既能奉献激情的生命体验,又能奉献具幽默感的智慧,而谯达摩的诗又别出心裁地将禅宗的境界与结构的宏阔感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牛庆国、唐诗、杨晓茅、殷龙龙、李亚伟、大卫、鬼叔中、刘文旋、丁燕、三原、谭延桐、沈利、吴晨骏、老杰、草人儿、陆苏、贺建飞、王顺建、陈蔚、李云枫、华岛、沈杰、林木、唐瑜、丁郎、李师江、杨志、灵石、简人、王怀凌、江一郎、老刀、世宾、陈会玲、刘羊、周公度、刘焱、明星、沈风起、王乐元、片马、聂世威、任晓雯、吴德彦、皇甫小岛等众多诗人都呈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局面更呈多元化,更显示出这种"复合型"写作倾向无比开阔的艺术前景。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对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中的部分成员的诗歌写作倾向作一种宏观性的粗疏描述。在此需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上述对于写作倾向的描述属于一种典型的"静态分析",而非"动态考察",主要出于一种"归类方便"的批评策略的考虑。从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一个诗人对于语言的兴趣肯定会发生历时性的变换,他(她)极有可能在书面语、口语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混合体"所构成的开阔"词语的空间"进行各种"写作的实验"。换言之,一个诗人在一段时期内陆续尝试"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位于前二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是完全具有其现实的可能性的,而且此种情形在许多"晚生代"诗人那里确实也存在。我指出并强调这一点意在提醒并促使大家对于当下诗歌写作的丰富、纷繁的面貌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科学的理解与认识。
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诗学观念的"革命"一直在悄悄地酝酿、进行,至当下,已获初步的"成功"。当今的诗歌观念虽然五花八门,但在对词语、对技艺的高度重视和刻意追求上却显示出一种"语言诗学"观念的普遍认同,这是现代汉语诗学建构历史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更加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晚生代"诗人能够以纯粹、沉潜的态度投入诗歌写作实践中,并能从不同的写作向度自觉地体现或折射出那种具有本体意义的"语言诗学"观念。也就是说,"晚生代"诗人们普遍倾向于通过具体的写作行为来传达他们新颖的诗学观念(即诗人们常说的让文本"说话"),不像他们的前辈诗人们那样喜好对他们的诗学主张进行某种程度的舆论化炒作。这充分显示了"晚生代"诗人们更为理智(明智)与诚实的诗歌写作态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批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晚生代"诗人奉献出了大量坚实有力的诗歌文本,足以代表当下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从收入该诗选的250余名诗人的所有作品来看,其取材范围之广阔、其写作风格之丰富、其艺术品位之高档,都是颇为振奋人心的。如果我们认定"艺术和诗歌的消亡"只是一种虚妄和悲观的臆测,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纪汉语诗歌的重新振兴与繁荣,必将寄希望于这一代诗人们的执著追求与辛勤劳作上。
2001年7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