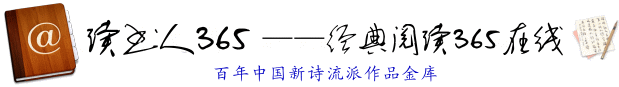
论"现代派"诗
□孙作云
(一)中国新诗的演变三阶段;(二)现代派诗的特点;(三)现代派诗作者;(四)现代派之成因及其流弊。
一
新诗人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算起,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整个的文学史上看来,这期间非常短促;但在这仅仅十年中,新诗却呈现着多样的姿态,试走过许多的道路。十年来新诗的演变,甚至比旧诗在几百年内的变化更为庞杂。到现在,像我们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欲知当时的"兴替之迹",已经恍若隔世,有些茫然起来。这原因一来因为老作家有的当了教授,有的亡命海外,都不声不响起来,若苛薄一点说,便是在这十年中的新诗,尚没有使我们永久不忘的好诗。到现在新诗走到最迷乱的道路,新作家们又各自标新立异,而新诗形式的不固定,也是造成混乱原因之一。我们虽然晚生了几年,不曾观光五四之盛,但只就新诗而论,似乎诗人们皆遵循胡先生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的老话,诗如果是这样作的,那未免太自由了,太容易了。然而我们的诗人多是这样的创作,而且这样的成功了。后来闻一多先生出版了诗集《死水》,以西洋诗的形式,参杂少许中国诗的内容,新诗的形式,因以紧严起来,内容也充实起来。而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他的态度的严肃。固然闻先生的《红烛》也是属于前一时代,但《死水》一集却为新诗演变中最大枢纽。若无《死水》则新诗也许早就死亡,而戴望舒先生的诗也不会出现,因为在形式上,戴先生的诗是对于新月派(姑且这样称它)诗的一种反动。所以我说《死水》是承前启后划时代的作品,而它的态度严肃便救了新诗的垂亡。
未说道本题之前,我把新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①郭沫若时代,②闻一多时代,③戴望舒时代。
第一期:郭沫若时代的作家,非常多,也非常庞杂。不过这时代的诗,意境与内容,尽管彼此不同,但其共通的特点是形式的不固定,不讲韵脚。在郭氏以前,胡适之先生为启蒙者,《尝试集》内,虽然也有几首好诗,但胡先生诗中旧诗的成份太多,有时候读起来,不由得便想起在读旧诗,或长短句,黄庭坚批评韩退之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适之先生的诗,也是因为才高而好。不过胡先生启蒙的勋绩,在文学史上是无人与之比肩的。与郭氏同时以作品名世者有朱自清俞平伯二先生。二先生新旧文学根源既深,所作新诗很能得新旧文学的长处。为初期诗人中最使人难忘者。
第二期的诗以闻一多与徐志摩两先生为代表。徐先生的诗是流利,清莹,华丽。读他的诗,如置身百花深处,美不胜收,又如听一个夜莺婉转的叫,使你的心不得不随着歌声跳动。但他的诗里,有几份才子佳人气,所以读起来,不令人满意。如《她是睡着了》、《残诗》、《再别康桥》等首,尽管有人赞叹不置,但我始终不喜欢。而志摩先生死前一二年的诗,态度既欠严肃,技巧又嫌拙劣,这大约是诗才将尽的缘故吧。和闻先生同派的诗人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的诗,意境与形式并茂,且不为人藩篱,最能表现自我的一位诗人,可称少年能诗者。这一派诗的特点,是形式的匀整,音节的调叶,且取材亦较他人为高。
第三派诗以戴望舒先生为代表。和戴先生同派的有施蛰存李金发先生。这派诗的开端是周作人先生译的法国象征派诗人gourmont的西蒙尼(后来收入陀螺里)。这些诗又被戴先生全译一遍,登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周先生又译了日本一茶的俳句,也给这派诗人许多影响。戴先生又译了法国象征派后期诗人保尔夫尔的诗数首登于《新文艺》上(水沫书店版)。这派诗是现在国内诗坛上最风行的诗式,特别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新诗人多属于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因为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二
现代派诗的特点便是诗人们欲抛弃诗的文字之美,或忽视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他们的诗不乞灵于音律,所以不重韵脚,因而形式亦不匀整。从这一方面说,现代诗是新月派诗的反动。他们主张用新的辞汇,抛弃已为人用烂的旧词汇,但旧的字汇能有新的暗示力者亦用之。在这点上,使我们想起Horace的TheArtofPoetry的论用字的一段。郝氏便主张他人用俗了的了,应该抛弃而创造新的辞汇。更主张旧的字有新的刺激力者亦应用之。他更说明辞藻语汇,也正像树叶一样,在春天里生长,在秋天凋落,所以它也是沿着变化的,生存和死灭的道路走。现代派的诗人们很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主要写新的题材--前此为诗人所不屑注意的事物,他们用来当题材。这一点扩大了诗的天地,是这派诗人对于诗的贡献。实在说现代派诗是一种混血儿,在形式上说是美国新意象派诗的形式,在意境和思想态度他们取了十九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态度。新意象派诗无异议的是都市的文学,他们之取舍题材,是以物质地的标准来取舍。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都市的诗作。中国的现代派诗只是袭取了新意象派诗的外衣,或形式,而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意境。所以现代派诗中,我们很难找出描写都市,描写机械文明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他们所写的多绝望的欢情、失望的恐怖、过去的迷恋。他们写自然的美、写人情的悲欢离合、写往古的追怀,但他们不曾写到现实社会。他们的眼睛,看到天堂、看到地狱,但莫有瞥到现实。现实对他们是一种恐怖、威胁。诗神走到这里便站下脚跟,不敢再踏进一步。在一方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为文句而歪曲了或牺牲了"意思",又确是一种新的为艺术而艺术。
戴望舒先生的《望舒草》是这派诗的典型作品,直到现在我不知看见多少青年诗人在模仿它,甚或窃取他的片句只字插在自己的诗里。他的《望舒草》便最能表达他写诗的主张。为明了这一派诗的特点起见,所以不得不引用《望舒草》中诗札内较重要的几条:(原题为《望舒诗论》登载于《现代》二卷一期)
一、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去了音乐的成份。
二、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五、诗的韵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七、韵和整齐的字句,会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
八、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和超官感的东西。
九、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十、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作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
十一、只在用某一种文字写来,某一个人读了感到好的诗,实际上不是诗,那最多是文字的魔术。真的诗好的处,并不就是文字的长处。
戴先生的理论在中国新诗发达史上,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但这些理论又有意或无意地与意象派诗的规律相同,布朗恩(Brown)在PoetryofOurTimes中述及意象派诗的六个规律:
一、采用日常谈话中的语汇,字眼应完全正确,不是近似正确,也不是徒然堆砌词句,就算了事。
二、创造新旋律--以表示新意境--不抄袭旧有旋律,旧旋律只能表现旧意境。我们坚持自由诗是写诗的不二法门,为了它奋斗和为自由而抗争的意义一样。我们相信一个诗人的个怀在自由诗中,常比在传统形式中表现得更好。在诗里新节奏就是一种新的意念。
三、题材选择,绝对自由。
四、表现--意象。我们不是画家的集团,但却相信诗的细节部分必须逼真,不应以模糊的概念了之。无论意义宏大也罢,音调悦耳也罢。
五、产生轮廓显明的诗,不写隐晦无定的诗。
六、最后,我们大半相信思想集中(Concentration)为诗之精要。
我们把二者对比,便可以许多因袭之点。那便是二者同主张创造新旋律,同主张新形式的自由诗,同主张诗的题材扩大,同要求新语汇。......在内容上亦多有相似处,如意象派诗的题材,写自然界的美。(意象派诗不是不描写都市和机器)意象派诗人中多深湛于东方诗歌,在形式上,部分地是受了东方诗歌的影响,如唐宋人诗,及日本俳句之类。意象派诗的首期领袖EgalaPound便译了许多中国诗,如李太白......《长干行》等诗。而东方的诗是以自然为生命,所以意象派诗与现代派诗多写自然之美及田园之趣。不过这种趋向,在现代诗中更明显起来,如许多诗人写牧歌,写田园诗。不过现代派诗究竟不是意象派诗,那便是横亘在每一个作家的诗里的是深痛的失望,和绝望的悲叹。他们怀疑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新的意识并未建树起来。他们便进而怀疑了人生,否定了自我,而感叹于旧世界及人类之溃灭。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洞,忧郁地,悲惨地,在每一个作家的诗里呈露着。这是现代诗的内容的共同的特点。到后来竟有诗人写肺病,吐血,思想的不健康,心里的病态,竟达到这样的地步。这一种世纪末的悲哀使少年的诗人们在法国象征派的诗中找着了同调。年来CharlesBoudlaire之被人歌颂赞叹,其根原即在此。所以我们不妨这里说,现代派诗是以意象派诗的形式为形式,而部分地
渗入了象征派的意识以为形式,而部分地渗入了象征的意识为内容。
三
首先要使诗者注意的便是在这里所举的十位诗人,有的旗帜鲜明地表示隶属于某派,但有许多年青的诗人,只有模糊的貌似,我们可以说只有一种"倾向"(Tendency)而没有真正地属于那一派。他们的年龄是年青的,他们的"身分"是涡移的,他们的人生观思想是不确定的,他们的形式也没有固定,他们可以向种种不同形式的诗探试,所以把他们硬安排于某一作家群,在作家自己或不承认,在我也有些不忍。因为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批评者不能像命运之神生生地派定他们的前途。其次,我们在这些作家中的作品里可以看出许多模仿或暗袭他人的痕迹。老作家有的直接从西洋诗里,抄袭了人家的意境,甚或字句。而新作家又很显露地抄袭了老作家的东西。我们不防说这是"模仿"。这并不足以诟病,因为完全为自己所创造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并不存在。像魏文帝在《典论论文》所说的"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现在还不敢希望有这样的大作家。我们只希望于辞有所假,而能假得好;于学有所遗,但并不完全空空如也就够了。现在举出十位诗人来,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及莪珈,何其芳,艾青,金克木,陈江帆,李心若,玲君。约略的说一下。
《现代》的前身是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所以《新文艺》的第一卷上的诗,便是后来现代式的诗。不过《新文艺》较有前进的意识罢了。戴望舒的诗在《新文艺》上登载了不少(后来收在《望舒草》里),但这时期他有一首好诗,使读者们永久不能忘记便是《我们的小母亲》,这首诗在他的诗集中,不失为最好的一首。因为原诗很长,故不便征引。还有姚杉尊先生的《列宁格勒的风》也是一首完整的好诗。前一段:
你忧郁着什么,田园啊?
忧愁那晚焰的金黄,水蓼花的绯红,
燃不起农民们乐天的好梦,
到处都充满着犁与锄头的反叛与骚动,
再没有从前那样忍饥受寒的悠悠的古风?
我知道,忧郁的田围,你是心怕
那像海风一般卷着过街头的
像铁链底环,那样紧结着的农民的队伍。
......
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是一首好诗。可是姚先生在文坛上的影子好像从此不再与读者相见了。
戴望舒是这派诗的主要提倡者。他译了福尔保尔的诗,译了果蒙的西茉纳集,《望舒草》的后半部诗都登载在这里,是戴先生诗风转换后的作品,戴先生写诗又是有理论的(《诗札》,所以很能表现统一的情调和形式;在诗的内容也有统一的思想绵亘着。明眼的读者一看便可以指出那便是横亘于作品中的虚无的悲观的思想。这大约是戴先生的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因为有"统一的"思想,所以我们谈他的诗,能得着同一的色调。这便是望舒的不可及处,在中国新诗人中真是凤毛麟角。王世贞批评陶渊明诗:"渊明托旨冲澹,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后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艺苑卮言》)望舒的诗为什么能表现统一的情绪或色调,便是能自大入思来!而望舒的模仿者便只取其貌似,所以是不好的。
在《望舒草》好诗当然很多。(《雨巷》也是一首好诗,但属于前一期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记忆》、《对于天的怀乡病》、《游子谣》、《乐园鸟》、《林下的小语》等首。
施蛰存是首先明白地提出(《现代》第一卷第二期)"意象抒情诗"的旗帜,也是这派诗人中有力的提倡者。他虽然没有出诗集,但他的诗我们还记忆了许多首,如题为《意象派抒情诗》下的几首:《桥洞》、《祝英台》、《夏日小景》、《银鱼》;及《九月诗抄》题下的《嫌厌》、《桃色的云》、《秋夜之檐溜》。而《桥洞》一诗尤好,很能作到情绪的抑扬顿挫,给读者以意境的美(诗长不引例)。
李金发的诗是近似于象征派的,但我也把他算在现代派诗人中。理由:第一他的诗多是自由诗,与现代派诗形式上相似,第二思想上也表示着悲观的虚无思想,在竟境上也多有相似处。本来文学上的派别,只是一种部分的近似,绝对没有完全一样的作家群,所以把李先生归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潜分。他的诗的特点在技巧上说:(一)是最善于联合不相属的奇特的比喻于一个观念上,而能给读者一种新的暗示力(SuggestivePower),这是作者最大的成功处。本来诗的巧妙,即在联合相属的观念于一处,而能有一种新的力量。(二)在意识上,李先生的诗多描写人生最黑暗的一面,最无望的部分,诗人的悲观气分比谁都来得显明。如《太息》。
"我知道终如要死的,从此
人类忘记我的颜容,与自苦的努力,
但你该留下那美丽康健的人儿,
香花远树,摇曳于天空的柳梢,
他们得因长寿,
好去讥笑我的短促的挣扎
"我恐怕我的衰老的伛偻来临,
我忧郁不自爱的人类
在我的身后崩毁。......"
(三)因为人生失望更进一步怀疑了理智的存在,更进一步欲逃避现实。《忆》诗中:
"你是界间的大哲人
你说出万古不朽的真理
表现出人间伟大的恩爱,
牢记者,这些就是幸福
勿使阻险的智慧毒害你。
"我欲置你有宝殿之深宫,
我欲携着提琴挈你行走
我欲诱你遁迹于世界之他一角。"
(四)充分表现知识阶级的伤感气分。下面几句诗又把他写诗的态度,表现无遗。《太息》:
"每当微细的现象,使我诗笔流泪,
常有伟大的胜力使我漠然,
一贯的矛盾,以生命作尝试。"
这几句话,说明现在诗人的写作态度及其矛盾,最为扼要。李先生近三年来的诗多登载在《现代》上,如《月夜》、《忆上海》等诗,而无疑地以《夜雨孤坐听琴》为诗人最得意的作品,这首诗是近三四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莪珈在一卷五期上登了诗三首。《当黎明穿上了白衣》,不佳。有似五四时代的诗。其后两段: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上是这么新鲜。
看,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
看。"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筋疲力尽,索然无味了。但《阳光在远处》描写抑郁的不快的暗淡的景色和心情最好,却无疑地是一首好诗。
何其芳君的诗,在这两年里我们读到很多,如登载在《学文》、《诗歌与批评》、《水星》的几首,又没有一首诗很坏,是近二年来大应注意的新诗人。他的诗的特点是很能婉转地细腻地抒写年青人的脆弱的易感的心情。《现代》上登载了他的诗二首:《有忆》及《季候病》,而《季候病》尤佳。
"说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声否,
说是一种刻骨的相思,恋中的征候,
但是谁的一角的轻的倩媚的裙衣
我忧郁的梦魂,日夜萦系
谁底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铃声,
呼唤她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
......
"过了春又过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
迷漠的怀想着,不作声也不流泪。"
艾青的诗只看到一首《芦笛》,但这一首诗已使艾青君在文坛上有了地位。他的诗完全不讲韵律,但读起来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力。他的思想更为急进的;这是一首有力量的诗。写一个青年如何唾弃旧世界而讴歌未来的新生。
"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地
从灼闪的火焰里伸出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去,
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
而且我要将他高高地举起,
以悲壮的Hymn,
把他送给海,
送给海的波,
粗野地嘶着的
海的波啊!
金克木的诗有一个显着的趋向,便是有意地无意地在学乐府诗。他的意境是苍老的。背景多取材于古代的事物。如《晚眺》、《古意》、《眢井》、《黄昏》、《灯前》。如《古意》:
"又要在灯前忙于刀尺子--枯叶已铺满云山。
前宵说鸣枭不吉,
今日说不管他夜单。
妾薄命,啼笑难!"
任你们到别院去取乐吧
只恐辜负了舅姑。
前宵辞去熟识的机杼,
今日提起生疏的小锄。
且上山,采靡芜!"
这首诗不能算好,不过为表现代诗之另一种作风所以引来。金先生的诗,据我看到的以《黄昏》一首最好。
陈江帆的诗又是极明显地趋向田园一方面。他的诗富于牧歌的气分,为其诗的特点。陈先生的诗,字句很严整,典雅,表显亦十分细腻。他的《荔园的主人》、《缄默》、《夏的园林》、《秧尖绣的海》几首,技巧上均使人满意。而尤以《秧尖绣的海》最好,读者最宜注意。
李心若的诗表现青年更深切的失望。他怀疑了一切,即对于自然,亦发生憎恶。如《倦》:
"在我天堂的花草,很好吧,
也不愿为仙,而只要永久的寂灭。"
在《听歌》的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不会泛上诉情的颜色了,
我以僵木的脸暴露人间的悲哀。"
玲君的诗尚不多见。就已读过的几首,技术上均称满意。如《二月的Nocturn》、《大街》、《白俄少女的guiter》、《忧愁夫人》,而以《音乐之感谢》最好。
"摇摆的伞下散射着
一线地,无敬线地
模糊的音乐之雨啊!
"冲积下,沉默这么久,
火山的石层
隐藏的么,如今被挖掘出来了。
看不见飘,飘在模糊中的音线
听着黯然的,呜咽的雨,
已经漂流得这样远了。"
以上算把几位诗人约略地述过。有几位新诗人,因为作品的少见,所以更不得不只凭着读过的一两首。我知道这是不足凭的,因为作家们的思想及技术,恐怕连自己也是模糊的。我深切地相信这些年青的诗人,有伟大的未来,能给诗读者以更好的果实。
四
文学流派的发展,或相互嬗递,是循着曲折的道路进行着。向来没有走过一直的路径,或恰到好处的路径。某一派在盛时校正了前人的错失,而此派的余流又变本加厉地进行着,不知自己也走歪了道路;于是又有新的派别出来校正。这样互相更迭着,形成了一部文学史。文学的发展,无疑地也是辩证法地进展着,没有一成不变,没有止于至善之境。新诗在第一期,因为反对旧诗的严格,所以"过分自由"。这是对于千余年来旧诗的反动,所以韵律,形式,安全不讲。故新诗等于说话,等于谈家常,结构既不谨严,取舍更无分寸。新月派的诗人们出来,力矫此弊,形式也因而固定,这是对于五四时代新诗的反动。新月派诗不久又被人厌恶了,甚有人名之曰"豆腐干体",所以现代派诗人出来,主张自由诗,摈弃均律,不以辞害"意",这是对新月派诗的反动,此其一。一般地说来,现代派诗是对于整个的旧形式的均整及旧题材的反动。诗人们的题材多雷同,千篇一律,已失去诗的刺激力。故一变而回复到田园的题材,牧歌的原始的追怀。生在二十世纪都市的人们,如果拿起三百篇的"风"诗和旧约上的素罗门歌一读,换换口味,倒真能逸兴遄飞。这里有一个文学的根本原理:那便是人们读厌了或作厌了形式均整和意境雷同的诗,往往希望有形式疏散,意味新莹的诗出来代替。沈休斋说"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现代派诗中,为什么多写田野,园林,牧歌,便是这种要求"野意"的表现。此其二。中国语文多是单音字。所以力求形式的齐整及声调的铿锵,除非你作旧诗,不整齐的字句中很难有音调的叶调。如果译过几首西洋诗的人(以新诗形式译出)马上可以看出其中的困难。这也是现代派诗之形式盛极一时的原因。此其三。
在内容上说,一、现代派诗多表现着悲观厌世的思想人生的空虚,无边涯的黑暗横亘在每个作家的心里、诗里。如戴望舒先生在一九三一年还写着《我们的小母亲》,但后来这样的诗,永不曾出现于诗人的笔底。这因为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国政治的高压。但诗人们又多生无媚骨,不能马上满意现社会,所以每个作家都陷入于绝望的泥泊里,辗转着,呻吟着,吐不出一口气。又因为民国二十年的东北事变,悲惨的古国,随时有被人灭掉的可能。不年余失掉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知识阶级是明白敌人的力量和自己国家的势力。但是怎样应付敌人呢?全无办法!所以不悲观又怎样呢?现代派诗所以表现悲观的虚无思想,原因在此。其次,现代派的诗最能适合"读书人"的趣味的。因此在这三年间作家倍出,在文坛上盛极一时,形成一个大派别。这种趣味是新的为艺术而艺术。
流弊。我已经说过文学流派的更迭,在其初多是校正前派的过失。但此派不久又发生流弊,而为新派所替。现代派的诗,老作家如戴、施辈,虽然主张诗不能借重音乐的成份,但他们的诗,仍是流畅可读;音调并不生涩。他们虽主张自由诗,但不是没有结构的,形式也极谨严。到后来的作家们便没有作到这几点。此派之失:(一)字句异常生涩,并非不好懂,(二)过分忽视音节,读之拗涩,不能上口。(三)无组织,无结构,失掉了Concentration,形式过于散漫。诗人写诗固然有许多兴到诗成。如天衣之无缝;但组织结构是有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体,并不是徒然的字句的堆砌。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里,有时可拉长数十句,有时可缩削成一两句,这样的诗是万万要不得的,任何是什么什么派。(四)趋向于病态的题材。如张君的《肺结核患者》:
"送丧地似地
披上了素白的衣服了。
"然而玫瑰也一朵朵
开在苍白的唇边了;
"血的玫瑰,枯萎地
在丧钟里颤抖着了。"
即使天地间再没有"玫瑰"了,我们永不愿欣赏着而且歌咏着这样的"玫瑰"。我们不忍得写这样的诗去戕害青年。当然我也知道诗国里并不是美好的幸福的事,同样我也知道诗的题材不应限定于狭窄的一面,诗国要求更广大的天地。(五)新作家的诗多是咀嚼着老作家的唾余,而没有新的进展。我们读意境雷同,题材雷同,甚至字句雷同的诗太多了。新诗人们为什么只能给读者这样贫乏的食粮呢?我们觉得这是值得惋惜的。
最后我要求这样的诗歌:
①内容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
②意境凄惋的诗固不摈弃;但更要求粗犷的,有力的诗歌。
③使字句的抑扬顿挫(汉赋便能作到这一点)和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相辅并行。
④要求形式更谨严的诗歌,而不是造作的均整。
⑤无别字错字的诗歌。
⑥表现时代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