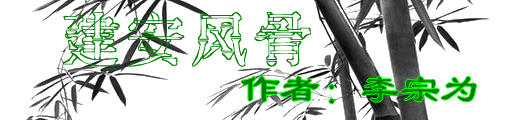
建安时代的咏物赋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竦芳柯以从风,奋纤枝之璀璨。其始荣也,皦若夜光寻扶桑;其扬辉也,晃若九阳出旸谷。
这是曹植《芙蓉赋》中的开头一段。一开始,作者就标榜芙蓉,亦即荷花,在百花中居于“独灵”的地位。它长长的根株植入深深的土壤,它的茎叶浮泛在清清的流水中。微风吹拂下,荷花的茎叶竦然摇摆,闪烁出璀璨的光泽。当它刚开花时,那深红色的花苞宛若落日般鲜艳;一旦繁花盛开,那怒放的花朵,又像朝阳那样明媚。这里“扶桑”指的是神话中太阳落山后栖息的扶桑树,“旸谷”则是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地方。神话中又有羿射九日的故事,所以这里说“九阳”。
我们可以看到,在《芙蓉赋》的这段文字中,作者句句写的都是荷花,同时又句句都在影射自己。写荷花结根重壤,擢茎清流,是隐喻作者学植深厚,志趣清高;写荷花茎花朵之璀璨美丽,是形容作者人品才华的皓洁高尚。这一类在字面上专咏一物而实际上用以自喻或喻人的赋作,以往没有专门的名称,我们姑且称之为“咏物赋”。
这个名称,笔者承认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因为“赋”这一文体,虽然是骚体之苗裔,但自它独立以来,依陆机之见就以“体物而浏亮”而与“缘情而绮靡”的“诗”分道扬镳了。既然它本以“体物”亦即描写物象为特征,那么在它里面又何必分出“咏物赋”一类呢?
然而,笔者采用这一名称,也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赋虽然以“体物”为归,但在古代,这一“物”字实有非常广泛的涵义。即以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赋荀子的《赋篇》而论,其中所分别铺陈的就有礼、智、云、蚕、针等五种东西,里面礼、智两种,以今天的概念就很难归入“物”类。到了西汉时代,以抒情为主的骚体的楚辞与赋合流,赋的流品就更加复杂,像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无论如何难以归之为“体物”的。枚乘《七发》,分述七事来启发楚太子,其七事为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等,其中所着力铺陈的田猎和观涛都难以归之于“物”。两汉大赋的体制内容,大抵与《七发》相似,只是增加了山林、物产等内容而在铺张夸饰上又进了一步。同时,其间的一些小赋则仍以抒情为主。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失宠妃嫔望君不至的复杂心情,张衡《归田赋》述归隐于田野的欢快,都以描写人物
的心情为旨归。两汉赋中也不乏叙事之作,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等等都叙述作者的一次远征,然后描绘一路所见的景物,又就所经各地的史事抒发内心的感慨。所以赋的题材早已十分广泛,很难用“体物”来总括它了。
并且,就是以“体物”的一类而言,有的罗列万象,有的专写一事,也应加以区别来明其不同。鉴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赋是古代诗体中的一种,在题材上它与其他诗体没有重大区别,同样可用来记事、抒情、咏物;它与古代所谓“诗”的区别,除了形式上的不同外,它又偏长于铺陈描写,这是它的特点。其中在魏晋以后逐渐成为主流的,专就一事一物来铺陈描写以“体物写志”的,笔者姑且以“咏物赋”名之。
我们已经看到,咏物赋发端于荀子的《赋篇》。荀子《赋篇》分咏五种事物,每种事物都铺陈描写一番它的功用情状,最后才说出这一事物的名称,有些像谜语的样子,里面有说理的意味,却没抒情的成分。如其中说针的一段云:“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纵,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理。夫是之谓箴(针)理。”
汉初贾谊的《鹏鸟赋》与荀赋不同。鹏鸟即猫头鹰,当时已认为见之不祥。贾谊谪居长沙三年,有一鹏鸟飞入他的居处,贾谊因此作了这篇《鹏鸟赋》,在赋中假托他的问话和鹏鸟的长篇答辞,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思想来排遣他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文中虽有抒情成分,但仍以说理为主,并且虽以“鹏鸟”名篇,其中却并没有对鹏鸟本身作任何描写,鹏鸟在文中只担任一个对作者谈论老庄思想的角色而已。如果说荀赋像谜语,则贾谊此赋近似寓言。
到了建安时代,情况大大改观。首先,咏物赋的大量出现是以往偶一露面的情况所远远无法比拟的。以建安七子所作为例,现存建安七子的赋(包括残篇)近七十篇,其中咏物赋就多达三十篇左右,占全部赋作的半数,可谓盛况空前。其次,在建安时代的咏物赋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对所咏事物的铺陈描写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志,荀赋和贾赋所同有的说理成分则大大削弱,至多不过是抒情的陪衬而已。赋到这时,才真正成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的“赋者,铺也;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的样子。
建安时代最早一篇著名的咏物赋也许是祢衡的《鹦鹉赋》。建安初年,祢衡得罪曹操、刘表后到了江夏太守黄祖处,在最终因辱骂黄祖而被黄祖杀害前,他曾一度为黄祖器重,黄祖的儿子黄射也与他很接近。在一次黄射召开的宴会上,有人献来一头鹦鹉,黄射很高兴,请祢衡即席作赋娱宾,祢衡就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地作了一篇《鹦鹉赋》。在赋中,他描写了鹦鹉因不同于众禽的奇姿妙质而被罗致幽禁于王公贵人之家的遭遇,借以抒发了有志之士在群雄割据的离乱时期不得不委身事人的那种委屈苦闷的心情。祢衡此赋一出,在当时影响极大,比他稍后的曹植以及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阮瑀、应玚等都作有《鹦鹉赋》以规拟之,因此可以说此赋为建安时代咏物赋的盛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曹植也是对咏物赋的兴起贡献极大的人物。曹植亲自编定的作品集,收赋七十八篇;原集散佚后,今存南宋刊本中计有赋四十四篇(包括残篇),则佚失者将近半数。然而,即以今存赋篇而言,其中还有十七篇是咏物赋,可见他在咏物赋上用力之勤。
现存的曹植咏物赋,除少数是逞才炫博的应酬之作外,多数是抒发他愤懑失意的感情的,如《神龟赋》咏神龟之“终遇获于江滨”,“归笼槛以幽处”,感叹“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难烛”;《蝉赋》咏蝉清高无求而危机四伏,抒发作者无辜见疑、忧谗畏讥的悲愤心情;《离缴雁赋》写被猎人射中的雁,借以倾诉作者孤独无援的悲惋之感;《蝙蝠赋》则通过对“形殊性诡”的蝙蝠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嫉邪愤俗的感情。曹植的这些咏物赋都继承了祢衡《鹦鹉赋》的创作方法,既贴切生动地描写了所咏的事物,又具体形象地渲染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以描写之贴切生动而言,曹赋比祢作也有所提高,如祢衡《鹦鹉赋》述鹦鹉被捕获后悲痛与雌鸟、雏鸟的隔绝云:“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悯众雏之无知。”曹植《鹦鹉赋》则云:“身挂滞于重笼,孤雌鸣而独归。岂予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相比之下,曹赋虽有模仿的痕迹,但在描写上更加贴切鹦鹉的身份,因此也更加生动形象。
曹植的咏物赋中,有一篇《鹞雀赋》非常特殊。它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赋篇之以六言为主,通篇都是四字句;内容上它也与他赋之侧重于铺陈描写不同,而是以鹞与雀二物的对话,构成了一则寓言式的小故事。它的大意是:鹞想捕捉一头雀,雀自称体微肉少,恳求鹞不要捕它。鹞以“三日不食”之故,拒绝所请。雀闻言悲鸣,又飞入一株茂密多刺的枣树,鹞就舍弃它而去。此雀死里逃生,立即去向自己的配偶夸耀自己如何敏捷,如何能言善辩。此赋以文字俚俗的四言句式,叙述了一则讽刺临事慌张、事后又沾沾自喜的小人的寓言故事,与其他所有文人的赋作在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与六朝残存下来的民间的故事赋《宠郎赋》在各方面都相同。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这篇赋是曹植摹仿当时的俗赋写成的。在敦煌卷子中,有一篇题作《燕子赋》的俗赋,写黄雀侵占燕巢而被凤凰责罚的故事,其文字也以四言为主,黄雀无赖之状也近似于曹赋中的雀儿,也可作为《鹞雀赋》出于俗赋的旁证。另一篇《蝙蝠赋》,也都是四言句,但文字较为雅驯,可视为曹植汲取俗赋形式写作文人赋的进一步尝试。可惜此赋只残存一小部分,已难以窥见其全豹了。
建安时代的咏物赋,以曹植所作成就最高。曹植的咏物赋不但词藻华赡,并且笔致清新浏亮,形式活泼多样,削尽以往许多赋作因铺张过甚而繁复板滞的积习。对于后来咏物赋在赋体中蔚为大国,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当首屈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