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1)
|
似乎是对整个中国诗歌形式上的一个总结,《红楼梦》几乎写遍了骚体、汉赋、唐诗、宋词等等诸种韵文的美妙。虽然在一部叙事作品中插入韵文往往具有华彩意味,但这里的每一个华彩段落都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性和强烈的叙事性。当人们在倾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大段大段人物独白时,他们感受到的仅仅是人物的情感思想以及复杂的内心活动,但一旦进入《红楼梦》诗词曲赋的阅读,人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读到的远不止是这些内涵。换句话说,如果删去莎翁戏剧品的独白部分,其所叙述的故事依然完整无缺,但如果抽掉《红楼梦》中的所有韵文部分,那么叙事就会变得残破不堪。韵文之于叙事的这种整体性,也许是《红楼梦》的又一独特之处。这不仅在西方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的韵文,在《三国演义》《西游记》或《金瓶梅》等小说中不过是人物形象、山川湖海、或者云雨私情的渲染和描绘,而整个故事的叙述却在这种当口停格,等到诗意挥发完毕,画面才继续流
动。
《红楼梦》中这种韵文部分的独特性在叙述韵文和人物韵文这二个层面上同时展开。所谓叙述韵文指的是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所插入的一首首诗作,所谓人物韵文指的是小说中诸种人物所抒写的一次次吟唱。相形之下,人物韵文的比重远远超过叙述韵文,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其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上人物韵文在整个韵文部分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我想把这一章的讨论集中在人物韵文上,仅仅捎带论及小说前四回中的叙述韵文,至于第五回中的“红楼梦诸曲”则留待论说人物形象的章节细加推敲。
我认为第一回中所插入的一些韵文,主要是为小说的整个叙述定调的。这种定调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好了歌”和“好了歌解”,一是“顽石偈”和“题石头记”以及第三回中贾宝
玉亮相时的两首“西江月”。
一首“好了歌”,以及反复咏唱的方式道出一声声长吁短叹,主旨在于诸色皆空;而一篇“好了歌解”则是委婉舒展,细细讲述色如何而空的秘密。空的意象经由如此唱叹,人们可以领悟到,与其说是佛门中的四大皆空,不如说是一种寂灭的命运,以及对这种命运的领略和感慨。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空的意象是四大皆空的话,那么不仅是那番感慨,而且连小说本身都不可能成立。因为在四大皆空面前,人们无言以对。惟有面对寂灭的命运,才会发出如此的感叹,才会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如此不辞辛劳地写出这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可见,诸色皆空的正确注解应是此空即色;而色如何而空的实质性意味则在于空如何见之于色。也即是说,因为空的寂灭意味,才有了如许的悲怀愚忠,才有了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所以我说《红楼梦》乃命运之作。
这样的叙述基调同时又以“顽石偈”、“题石头记”和描写贾宝玉的二首“西江月”的顽石——作者——人物的和声形式展示出来。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请谁记去作奇传?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从“顽石偈”的苍天红尘到“题石头记”的荒唐言辛酸泪再到人物形象造型的西江月,正好构成顽石(灵魂)——作者(梦幻)——人物(情种)这三个基本叙述元素组成的叙述和声。这三组诗歌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互相展开互相注解,从灵界到梦境再到尘世层层铺叙又互相环绕。它们将顽石——作者——人物三位一体的形象造型以韵文形式展现出来,同时又直接标明了灵——梦——情的叙述元素的叙述结构。如果说,灵魂自叙是《红楼梦》的叙述基调的话,那么这三组诗歌则是其叙述结构的展示,而前面的“好了歌”和“好了歌解”所阐释的色空意象则为这样的叙述基调和叙述结构规定了必不可少的叙述前提。
好像生怕读者不能读懂这样的叙述前提,小说在第一回和第四回中又特意以贾雨村的“对月寓怀”和“护官符”对色空意象作了有力的反衬。一则是“满把清光护玉栏”,一则点明所护“玉栏”者,官符也。没有这种雄心壮志的抒发和四大家族的显赫声势,那么上述三组诗歌尽管具有和声效果,但毕竟还缺少必要的参照系。但有了这样的反衬,整个叙述基调就好比在一片黑暗之中推出的一道光芒,既照亮故事又照亮故事的叙述,具有极其生动的立体感。贾雨村的野心和护官符的威严构成一种浓重的世俗的暗色调,而小说以灵(顽石)为纲的叙述基调则如同伦勃朗画面上经常出现的一束光亮,圣洁,超拔,具有崇高的神明意味。相形之下,《金瓶梅》那种惩恶劝善式的叙述基调就显得十分肉感,充满世俗的市民气息。顺便说一句,我很奇怪过去的一些红学家们那么起劲地把《红楼梦》和所谓市民阶层联到一起,因为无论从总体精神文化内涵还是从叙述方式写作风格上说,这部小说洋溢着的绝对是贵族气息而没有丝毫市民腔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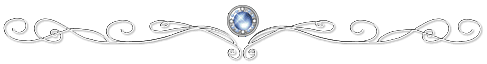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