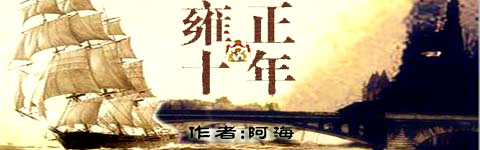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却说那晚,蓝旗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带领数个大班和军官,还有一位中国海关的胥役,夤夜从虎门附近赶往广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黄埔关的海关人员帮助之下,在停在黄埔的一条中国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他们告别了中国船上好心的船民,继续划着舢板船,向广州进发。
从古黄埔锚地到广州,路途不远,大概是十几里的水路。舢板船毕竟行驶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终于到了广州城外的水面上。广州贸易向来的规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数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广州;而且明确不得带火枪进广州。不过实际操作当中,在黄埔的大船上的船员,基本上都可以到广州来开开眼界,因为外洋船在广州建立夷馆之后,通常借口守卫夷馆,让船员轮流到夷馆来住上一些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尽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内,洋人的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广州城外。古代广州城的西门外,向来是外商聚集之处。关于广州城西门外的历代对外贸易情况,研究很多,雍正年间的珠江岸线,应该比现在的岸线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贸区域旧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大致说来,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一条和珠江平行的大街为中心,两边都是商行和店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通常建在靠水一边。这样的洋货行规模很大,靠街这边,有大门和铺面,铺面用于收购货物;行内靠江边,则建有小码头,或者称为驳口,专门用平底船,将货物驳到黄埔。船到广州,要先经过一个海关的关口,才能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关口,是粤海关的总关,称为总巡口。
总巡口就在海关监督衙门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这样从各个洋货行运出的货物,必定经过总巡口,便于稽查。但是珠江水系复杂,为了防止从其他水道走私货物,在建有洋货行的江岸西边,同样设立了一个海关的检查口,名称非常形象和直接,称为行后口。
这也就是说,在广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区域,前后各有一个海关关口把守,中间沿着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货行和店铺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外国人通常称为镇子,Town,而把广州城,称为城,City,两者之间,区别十分清楚。但是中文当中,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广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货行的,也有指区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为贸易镇吧。外洋船到广州,带船前来贸易的领导人,也就是通常称为大班的,得以进入广州,在这个镇上开展业务。大班到镇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货行作保人,才能开展贸易,这是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规矩。所以坎贝尔等一众大班,未到镇上之前,就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由哪个洋货行作保人的问题。瑞典大班们提出讨论的行商,根据坎贝尔的说法,一共是三家。当然这三家,都是大班们熟悉的洋货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议应该找陈寿观的广顺行,因为广顺行眼下是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的洋货行。坎贝尔对陈寿观倒也没有恶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下子来了四条大船,英国这样的大公司,肯定会找财大气粗的广顺行作保。这样一来,陈寿观忙着为英国公司的这四条船服务,岂非容易忽视瑞典公司这样的小买卖?因此,坎贝尔明确地否决了莫福德的提议。
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船驳运到黄埔锚地,这样一来,岂非大费周折?所以张族观这个选择,也被否决。
雍正四年,坎贝尔和他的兄弟在一条港脚船上当大班,当时就以陈汀观的崇义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义行中。坎贝尔知道,崇义行规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里有十分便利的驳口。何况坎贝尔觉得陈汀观这个人,为人沉稳,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为欧洲人做好服务。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坎贝尔和其他大班们一起,轻车熟路地划着舢板,过总巡口,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