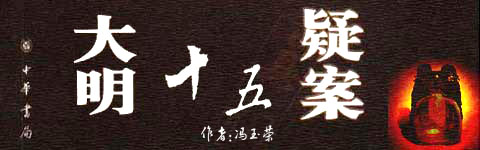故事自然得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台州宁海,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