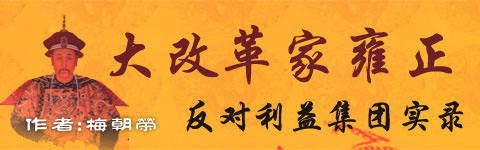整顿吏治,整饬财政
康熙帝晚年受“无为”思想的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即位后,为惩治贪墨成风的吏治,整肃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冒饷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私利的行为,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举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推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多项针对大利益官僚集团的工作。由于他态度坚决,措施得力,使得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办事雷厉风行的新型政府。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雍正帝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不愧为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
清查亏空,设会考府
康熙帝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地方绅衿鱼肉百姓,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时为雍亲王的胤禛对此情形已了若指掌。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有的多至数十万。他将其视为“负国营私”的大恶,决心要彻底革除这种现象。
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即位时,为表庆贺,经常要大赦天下,也即足颁恩诏,对国内各地实行一些惠民政策,或释放囚犯,或赦免钱粮,雍正帝也不例外。但当雍正帝看到恩诏中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列入时,大为不满,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贪官们的侥幸心理,若新君以此笼络人心,以后官吏侵吞钱粮的事就杜绝不了。雍正帝当即命令撤销这一条,并将清理亏空作为他即位后的首要任务之一。
雍正帝即位一个月后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的上谕。他说各地出现的钱粮亏空现象,不是受上司的勒索,就是自身的侵占,这都是违法的行径。在先,皇考圣祖皇帝宽宏仁慈,未能将赃官明正法典;一些勒令追补亏空的措施,也不过是虚应而已,亏欠现象依然照旧,国库因此而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拿什么去应付?此事关系非浅,因而要彻底清查。随后,雍正帝还特地部署了各地清查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期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
雍正帝又说:“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他省可知,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
即是说,在清查亏空中,除了惩罚勒索者以及挪移者本人外,假如有谁在清查中徇私舞弊,包庇纵容,万一被我查访到或被监察官员举报后证实,将连同该省的总督、巡抚一并治罪。比如山东省,以前查明的亏空有数十万两,虽然现在名义上用官员的俸禄补足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中间有不少巧取豪夺、乱收费乱摊派的事情。山东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对此,我是万万不会姑息容忍的。
雍正帝勒限三年,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总的说来,清查的成就比追补兑现的成就更为显著。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清查和追补工作做得较好的直隶总督李维钧报告清查出亏欠银41万两,至报告时已追补完成20万两,完成追补近50%。
其他各省拖欠未完者也有,雍正帝不得不将勒限再延长三年:“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无,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着该督抚奏闻请旨。”
第二个“三年计划”完成得如何呢?以对浙江钱粮的追补为例,雍正帝派性桂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会同督抚李卫协力办理,查核清楚,将积欠分年追补。雍正五年(1727年)、六年(1728年)两年,每年追补15万两,到七年(1729年)已将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的赋银77万两追补了40万两,其余的也可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雍正帝对此表示满意。
为了顺利完成清查亏空的任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发出了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所谓会考府,就是为清查政府亏空,打击官吏贪污舞弊现象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官吏审查机构,其职责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审计署。
雍正帝宣布此后一应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个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要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隆科多是雍正帝养母佟佳氏的兄弟,所以,雍正帝与隆科多本属外甥与舅舅的关系,但皇帝承认不承认、叫与不叫却是另一回事。雍正帝甘当小辈,尊称他为舅舅,这本来已经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雍正帝却叫下人都尊称隆科多为舅舅,这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大学上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这样就把奏销大权由原先的各部院收归中央,使得官员们想做手脚也不容易了。
为了能使清查政策很好地落实,雍正帝还特别对怡亲王允祥强调,要严格执行清查政策,不得有所松懈。雍正帝告诫允祥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雍正帝一再表示他对贪污等现象绝不宽容,至此,一场从上到下、由内到外,惩办贪官、清理亏空的活动迅速大规模开展起来。
会考府设立不到三年,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550件,其中驳回改正的有96件,占所办事件的17.5%。户部库存白银,经怡亲王允祥查出亏空共250万两,雍正帝立即命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及部吏均摊赔偿150万两,另100万两由现任户部官员弥补。
在清查亏空中,难免会涉及到贵族和高级官僚,对此,雍正帝一样不手软。不论何人,决不宽贷。一些王公贵戚、达官显宦不得不通过典卖家产用来赔偿亏空。康熙帝的十二皇子履郡王允祹曾经主管过内务府事务,雍正帝追查他的亏空,他没有办法补齐,最后只好将家用的器皿摆到大街上出卖,以便凑钱补空。康熙帝的十皇子敦郡王允也因赔银数万两,还不够数,被雍正帝抄了家产。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100余万两,由于没钱补足,雍正帝也毫不留情地抄了他们的家。
为了不使雍正帝失望,允祥严格执行雍正帝下达的政策,对达官贵人毫不留情。于是,人们便责怪他,说他过于苛刻,过于残忍。雍正帝听到后,说这不关允祥的事,进行严查是朕的旨意。雍正帝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达官贵人看到皇帝出头替允祥撑腰,即使心里有怨也不敢再说,会考府的工作因此得以顺利进行,达官贵人收敛了很多,中央各部的舞弊现象由此得到有效控制。
在中央清查工作展开的同时,地方清查也普遍开展起来。雍正元年(1723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江南粮道李玉堂等人。
雍正帝反对贪墨的工作仅仅开展了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六十一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帝治理腐败的肯定。
推行廉政,提倡节俭
雍正帝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反复强调,官吏的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为此,雍正帝大力提倡“廉洁爱民,奉公尽职”。
雍正帝还认为,一个人只有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为此,雍正帝告诫官员:“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为良吏。”
雍正帝所推行的廉政,是针对康熙朝后期官场的种种时弊而发的。晚年康熙帝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训,政宽事省,君主无所作为,官吏因循弄法,吏治败坏。尤其是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内外大小官吏或根据酬贿之轻重,补授好坏之官缺;或虚名冒饷,侵渔克扣;亦有大员子弟冒请军功,无功受禄。种种情弊,不一而足。雍正帝即位后决定整饬官吏,推行廉政。
雍正帝首先严厉惩办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以年羹尧为例,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银钱之多。除他的亲信外,谁想弄个一官半职,都要给他进献厚礼,有的一次送银多达二万余两。仅仅人事安排一项,年羹尧最多的一次就收受了四十多万两白银,那时一品大员一年的俸禄才一百八十两银子,这些贿赂可抵得上一万个八品官一年的收入!年羹尧这个“西北王”已俨然成为西北黑、白两道中神通广大、一手遮天、恶霸一方的大帮主。雍正帝调查清楚后,即对年羹尧进行了严厉惩办,同时也给其他官员敲响了警钟。
雍正帝对于贪官是毫不手软,而对于清廉刚正的官员则是倍加爱惜。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帝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并且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廉洁著称,雍正帝曾赐他御书“公勤廉干”匾额一方。李卫不苟同于官场积习,无所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员,这些人串通告状。雍正帝心中有数,指出: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
雍正帝虽然很重用清官,但他对清官也会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还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涉乎滥。固不可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
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用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在官场上,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名实兼收”。对此,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分析:“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即:这些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廉洁无私,实际上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应尽的民生职责并不经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关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可谓名利双收。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寒碜”,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逸,都把勤俭当作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应当说,雍正帝的确是一位胆识皆备、办事雷厉风行的皇帝。他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他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他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力倡廉政,整饬吏治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王朝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打响了第一炮,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严惩贪吏,雷厉风行
雍正帝在清查亏空的活动中查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为了肃清吏治,辟一朝清廉之风,罢官、抄家,是雍正帝对贪官们采取的严厉惩戒措施。
雍正帝采取的罢官策略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他们的常用手段就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帝要改革,是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凡是贪官,一经被人告发,就要革职离任,不许再像以前那样可以留任以弥补亏空。如果已经清还完毕,尚可为官者,由吏部奏请。
雍正帝严厉打击贪官方针的实行,使得被罢官的人很多。雍正三年(1725年),湖南巡抚魏廷珍上奏报称:该省官员被参劾的已有大半,如再查出舞弊问题,将继续纠参。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报告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无几。官员的频繁更换,原因之一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与罢官同样重要的手段是抄家。贪官一经揭发,雍正帝为使他们退出赃银,保证国库无损,主要采取抄家籍没的手段,这一招当然有效。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行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帝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帝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这固然表明了一部分人对雍正帝经常抄家举动的不满,但也表明用抄家作为对付赃官手段的行之有效。对人们的攻击和舆论的不满,雍正帝似乎并不在乎,把它们看成是阿其那(允)、塞思黑(允)等人蛊惑人心的狂悖之语。有时也为自己小小地辩解一下,说明抄家的必要:“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 音zi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乏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上有政策,贪官们便下有对策。对策之一是转移财产。说到转移财产,舅舅隆科多可谓是未雨绸缪,领先一步。他早就为自己留下预后之策,不等雍正帝对他下手,早就把财产分藏到京郊西山寺庙中和京城的亲友家中。贪官们的第二个对策是财产代赔。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有地方官和百姓代为清偿的。对策之三是借挪移来掩盖侵欺。所谓挪移,是指因公挪用,因为公务常常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等等;侵欺则是贪污。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亏空。但是二者性质有所不同,所以雍正帝在处分上也区别对待。一般来说,挪移是轻罪,侵欺是重罪。贪官们的这一对策是巧立名目、避重就轻,企图达到瞒天过海、浑水摸鱼的目的。对策之四是畏罪自杀。舍一己之命,力保万贯不义之财。
贪官有对策,而雍正帝更是先研究可能出现的对策,再制订政策,显然比贪官们技高一筹。
第一,命令亲戚帮助赔偿。这主要是针对财产转移提出的政策。雍正帝曾明确指出:有的犯官把赃银藏在宗族亲友之家,这些人平时也有分用赃物的,现在一定要他们帮助清偿赃银,同时也命令抄没这些人的家产。由于办法毕竟太狠,在抓不住实据的情况下打击有失准头而且株连太广,因此在实行了四年之后,雍正帝也觉得此法有些过分,将它废除了。从这方面也看出雍正帝是一个有错即改、实事求是的好皇帝。
第二,禁止代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由交情好的官员代自己先行赔偿,本来也没什么不行。然而做官的人人都想着占便宜,谁肯吃亏,代人赔了银子,事后难免肉痛,就有可能从百姓身上侵渔猎取,寻求补偿,巧借名目令地方百姓替官还债的情况多半又要发生。而且,获救的官员对出钱代赔的同仁必然感激涕零,这样又容易形成蛇鼠一窝,结成官场的朋党。虽然从财政上都能使国库亏空得以补充,但雍正帝的目的不仅在于补充财政亏空,还要杜绝官场陋习,不能顾此失彼,这便是雍正帝不许代赔的用意所在。从这里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深谋远虑与高瞻远瞩。
第三,挪移之罚,先于侵欺。 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得违规官员没有办法避重就轻。按常理,清查亏空,应当先抓贪污腐败,然后解决挪移问题,而雍正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规定在清查中,无论是侵欺还是挪移都要据实清查,而在追补赔偿之中,则不管是侵欺发生在前,还是挪移发生在前,都要先将挪移的亏空先补足,然后再赔偿侵欺的部分。雍正帝此计看似不合情理,实则高明。因为他早就看到了从前清查亏空的种种舞弊现象,贪官们偷奸取巧,将侵欺报作挪移,避重就轻,希望得以免罪。雍正帝对这种避重就轻的把戏早已了如指掌,他揭露这些贪官说:“借挪移之名,以掩盖其侵欺之实,至于万难掩饰,则以多者为挪移,少者为侵欺,为脱其量罪。似此相习成风,以致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雍正帝的这个办法一出台,就把许多贪官打了个措手不及,把他们的后路一下子给堵死了。这也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策略。事实上,在打击贪官清查亏空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雍正帝就逐渐恢复了往日先查侵欺再追挪移的成法了。
第四,对畏罪自杀的官员加重处理。贪官们常常以为自己身死就会一了百了,可是,在雍正时代,雍正帝是不会放过这些死了的贪官的。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帝说:这是赃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意思是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以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为使他们的狡计落空,雍正帝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雍正帝对贪官的查处,贯彻于他的整个执政历程中,并非虎头蛇尾或轰一阵子就收摊。雍正帝认为若是查一阵子就停下来,还不如不查,因为这样的话,被查的满腹不平,往往会“反攻倒算”;新上任的会在任期内大捞一把,吏治会更坏。当然,由于雍正帝抓住不放,到后来贪官自然是少了,但历年都有被罚、被办的贪官公之于世,如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学政俞宏图因贪污纳贿罪被斩首示众。
官场从来就是一潭“混水”,为了保护自己的皇位,历代一些皇帝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帝则显得格外地雷厉风行,甚至显得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不仅充盈了国库,而且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耗羡归公,弥补亏空
清理钱粮亏空,除了采用抄家的办法,让贪官的家人、亲友吐出来弥补外,它的另一个途径,则是用耗羡银来逐年弥补。
耗羡的征收和使用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相沿数百年的一项弊政。所谓耗羡,又叫火耗,是指在征收正项赋税钱粮之外的附加税。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既助长了官吏的腐化,也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雍正帝即位前,对耗羡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差徭和滥征滥派,早就看在眼里。即位后的新年元旦,雍正帝在给各个地方的文告中说:“今钱粮耗羡,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音juan娟)削何堪。至州县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雍正帝又说:父皇在世时,有人请加耗羡以补亏空,先帝未允,如今耗羡断不能加。由此可见,雍正帝在考虑既要削减耗羡又要用耗羡银清偿亏空的办法。
康熙年间,已经有人提出了耗羡部分归公的意见,但由于耗羡归公影响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考虑到必将引起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影响朝中稳定,康熙帝并没有批准实行。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耗羡归公的问题。他奏称: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勒派百姓供应,不如令州县官在原有耗羡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耗羡本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即如康熙帝所说是地方官的私事,杨宗仁要他们拿出一小部分归省里,作为公用,实际上是提出了具有耗羡归公意义的建议。雍正帝对杨宗仁的意见给予了肯定,表示甚为满意。同年,山西巡抚诺岷因该省耗羡问题比较严重,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通通上交布政司库,一部分给各官作养廉银。这是当初最全面实行耗羡归公的办法。
雍正二年(1724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奏: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由于办公费用都出在耗羡内,所以不用再从百姓身上打主意了。他的这一措施也是耗羡归公的办法。以前,雍正帝不太器重石文焯,认为他虚浮,看到这个奏折后,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此奏才见著实,非从前泛泛浮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作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就这样,在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下,山西、河南两省率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
雍正帝想在全国推广山西、河南的办法,然而又觉得难以把握,于是,他命令九卿会议讨论,把各自的意见奏报。结果有很多官员对此不赞成,内阁也做出了禁止提解耗羡的条奏。理由有三条:第一,耗羡是州县应该得到的,上级不应该干涉,更不应该全部收走。第二,把不是正税的耗羡也当作正税征收,让人觉得有增加赋税的感觉。第三,督抚公开允许州县征收耗羡,使属于私征性质的耗羡变成了合法,这是允许属下贪婪,而不是鼓励、教育属下。
内阁的这个奏议发出后,山西布政使高成龄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奏折中针对朝官们的理由一一析辩道:“州县官私征耗羡,以补官俸不足;上司没有耗羡,又不能枵腹办事,不得已就得向州县官要礼节常例,结果则还是出在耗羡项上,不如将之公开合法化,全省征收,给各官养廉银,形成定例,这样上司也不能再勒索属员,也省得州县官借口苛征里甲。”即:州县官通过私征耗羡,用来弥补自己俸禄的不足。但是,他们的上司不能直接收取耗羡,又不能空着肚子办事,必然要接受下面州县官所送的四时节礼,这礼还不是一样也出在耗羡项上?不如由全省征收耗羡,再由上司发给下属各官养廉银。这样做,上司就不能继续勒索属员,也免得州县官员有借口去苛征乡里。他又说:“耗羡归公,不是增加耗羡,而是要比原来征收的成数还要少征,况且耗羡归公,多征也不归州县,谁还滥加成数。”即:耗羡归公,不是再增加耗羡,而是比原来征收的总数还要少。况且,耗羡归公,多征又不归地方来支配,这样,上司也不再勒索下属,州县官也不会再找借口向民间征收苛捐杂税。他还说:大臣收节礼,甚至接受贿赂,这不是鼓励、教育属员的方法。不如公开地分配养廉银,共受皇上的恩赐。
高成龄针对当时耗羡滥征的实际情况,讲解了耗羡归公的种种好处。他指出,九卿所说看似有理,光明正大,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能让州县官员满意,而实际上是沽名钓誉,说得好听,听任州县官员狂收滥派,不讲做官的法规,不管百姓的死活,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能维持旧日的弊端。
关于高成龄的反驳意见,雍正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保证意见的公允,雍正帝又把问题交给总理事务的王大臣以及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讨论,并且一再要求他们讨论时应“平心静气,虚公执正,确议具奏”,同时警告他们,如果是心怀不轨或者意气用事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将有人要遭殃。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在这件事上是支持高成龄的。朝中大臣已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慎重商议。但由于这件事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人们自身的政治观念,所以反对的人依然很多。不但私下反对者比比皆是,而且还有不少人公开上疏驳斥,他们认为诺岷和高成龄的办法将会给今后官员的日常公务造成麻烦。来自山西省内的反对呼声也很高,持改革意见的山西官员势单力薄,感到压力十分大,政策的实行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实行了“必有一二获罪之人”的谕令,将持反对意见的刘灿调走,并革去其弟刘煜、刘烟的举人功名。
见到如此情形,有人提议“耗羡归公”先在山西试行一段时间,看效果怎样后再推广到各地。对这种意见,雍正帝给予驳斥,他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他这样讲,表明推行耗羡归公的决心不可动摇,不让臣下再犹豫。这种明确的态度虽然显得武断,但也成为了他行使政治权威的前提。由于雍正帝看到大臣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长期争吵下去将于事无益,雍正帝便做出了实行耗羡归公政策的决断。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六日,雍正帝发出上谕,首先批评了官员们的目光短浅,不懂得耗羡归公的重要意义。他说:“高成龄提解耗羡一事,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接着又历数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多祸害。他说:“ 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各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愿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雍正帝站得高看得远,比高成龄更深入。他认识到私征耗羡恰是造成下级营私、上级容隐、吏治不清的原因之一。上级一旦得到下级的实惠,必然会对下级的种种贪婪违法做法有所保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下级也必定有恃无恐,欲壑难填。这样吏治之败坏只会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所以应当全力消除这种弊端。实行耗羡归公,首先就有利于澄清吏治,而并非像内阁大臣们所说的那样是鼓励属员贪婪。
山西最先推行耗羡归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羡率就由原来占正税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山东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羡率高达80%,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后来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后又降至16%。河南同山东一样,原来的耗羡高达正赋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耗羡归公后,一下子降到了13%。其他大多数地区一般在5%~15%,耗羡率均较低。
耗羡归公之后,收入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弥补国家亏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实施的耗羡归公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耗羡归公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羡银从过去的暗取变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耗羡归公后,中央政府每年都从耗羡中提取相当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库亏空,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
再次,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转归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义统一拨付,或作为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弥补地方亏空,或用于赔补国库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耗羡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控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坐收坐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实行耗羡归公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耗羡归公后,各省耗羡率一般在10%~15%之间,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许多,人民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所以说耗羡归公既养了官,又安了民。
总的来说,耗羡归公是雍正年间推行的一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国力充盈,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设养廉银,杜贪贿行
在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大部分的耗羡银用在了补偿地方钱粮亏空的方面。后来,在亏空基本上被补足后,部分耗羡银就被转到了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上。
所谓“养廉银”,是指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办公中的实际问题,体现皇恩,从而在使他们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不贪污,保持廉洁奉公。
“养廉银”制度是基于清朝官吏俸禄比较微薄这一事实而实行的。清朝在京官员每年的俸银,一品官为180两,二品官为150两,三品官为130两,四品官为105两,五品官为80两,六品官为60两,七品官为45两,八品官为40两,正九品官为33两l钱,从九品官为31两5钱。另外,还按每两俸银给禄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银同于在京文官,但没有禄米;武官俸银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禄也只不过180两银子。每年发这一点俸银,不足以维持官员正常的生活,因此才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征耗羡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徇私舞弊、吏治败坏的局面。
当时,官员们贪污的手法多种多样,举不胜举。在诉讼中收取一定的贿赂是官吏主要的财源之一,民间所讲的“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在名义上是属于非法的。耗羡私征也是地方官吏的另一额外财源,是一项半合法的收入。康熙帝曾对河南巡抚鹿韦占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每两税银只取一分耗羡,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耗羡归公后,等于切断了地方官员的一条财路,而如果皇帝又没有增加俸禄,要想让他们正常生活,又要廉洁奉公,地方官员肯定会另谋他策。针对官吏们的实际情况,雍正帝指出:“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这就是说,雍正帝并不要官吏们空着肚子办事,而是要他们有合乎自己身份地位的经济收入。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官员们的高额补助,但官员们必须为官廉洁、杜绝贪污。于是,雍正帝决定把收取的耗羡一部分拿出来用来提高官员的生活,定期给他们发放一定量的养廉银,以求从根子上解决官吏腐败的问题。
不难体会,作为一朝新君,雍正常为当朝臣子们想得的确周到。在皇帝下面当差,若日子过得很清贫,不但失了臣子体面,就是皇上脸上也挂不住。这正是雍正帝的洞悉人情之处和为政风格,他凡事不搞理想化、口号化,而是从现实情况设身处地地打算,连臣子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极度重视,这也正是雍正帝善于驾驭臣下的韬略。
随着各地钱粮亏空逐渐得以弥补清楚,征收上来的耗羡主要是留作地方公用和留给官员作养廉之费,养廉银的发放数目主要依据官职的高低来确定,各省之间,由于政务繁简及赋税多少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另外,在这一过程中,雍正帝也逐步将养廉银的发放规范化、制度化了。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各省官员的养廉银数大致有了定额,同他们的俸禄相比,高出十几倍至一百多倍,可以说是相当优厚的。例如,原总督的薪俸仅为180两左右,其养廉银则高达15000~30000两不等。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总督的养廉银达到20000两,比180两的年俸高出100倍以上;江南总督的养廉银更是达到了30000两;最少的如福建、浙江、四川总督的养廉银也有13000两,其中大多数总督养廉银在15000~18000两之间。从二品的巡抚,养廉银也高达10000~15000两。正四品的知府,多者达到6000两,少的也有1000两。七品的知县,多的有2000~3000两,少的也有500~600两。与微薄的俸银相比,养廉银大大增加了官吏们的收入。
养廉银的发放让地方官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相比之下,京官的俸禄低微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对于这个问题,雍正帝也做了全面的考虑:如果京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京官仍然会向地方官吏索要,地方官吏也一定会向京官送礼,这样,养廉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扭转。雍正帝顾虑及此,于六年(1728年)下令,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新增的这一份叫“恩俸”。兼管部务的大学士也得双份俸银和禄米。在京的品级较低的汉族官员,原先每年只领禄米十二石,大多不够家属食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令按照汉官俸银数目多寡相应发放禄米,使他们不至花大价钱到市场上购买,后又给他们增加俸银禄米。这样,京官的困难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对耗羡归公一事评头论足了。
耗羡归公除了用于弥补亏空、发放养廉银之外,还用作地方上的办公费用,这一点在最早实行耗羡归公时就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提出来了。他说:“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用耗羡银支应。” 当时的湖广总督杨宗仁解释说,征收的耗羡一部分用来“充一切公事之费”,这样,就把每年的办公费用正式列入了政府计划之中。雍正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做出了总结:“将经年费用之款项、衙门事务之繁简,仪定公费,派给养廉,俾公事与私用,咸足取资。”意思是把地方政府的办公费也列为耗羡中的重要开支。
由于耗羡银是按地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的,而地定税基本上固定不变,耗羡银因此也就相对固定下来。同时,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和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因依照实际需要来确定,因此上下浮动不大,一般都比较稳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自己的收入以及使用都比较固定,计划的因素加强了,基本上也维持了收支的平衡。由此可见,核定办公费用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防止贪污,澄清吏治。它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从固定办公费用开始,一种数字化的精确的政府管理思维开始萌芽。较之以往粗放式的政府管理,办公费用固定化是政府在财政管理上的进步,也是对地方行政管理的一大促进。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社会有明显的积极意义。首先,养廉银的设置是封建国家和各级官吏在经济斗争中矛盾协调的产物,使用权既收归国家,又适当地照顾了官僚们的经济利益。其次,养廉银的设置是清朝特有的防止官吏贪污的一种经济手段。该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吏治有了好转,对清初因低俸而形成的腐败现象有所遏制。雍正帝曾说过:“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再次,养廉银制度的实施相对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整饬吏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取缔规礼,禁收杂费
雍正帝在实行清查亏空、推行廉政、严惩贪官、耗羡归公、实施养廉银制度的同时,还对官场中请客送礼、乱收杂费等陈规陋习进行了整顿。
官场上的送礼之风,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其作用来看,送礼既可拉近双方的距离,增进感情,又可满足双方的需求,彼此都甘之如饴。在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属,必须按陋规依照四时时节向上司送上一定数量的礼金。若上司本人身兼数职,下属就必须同时奉上几份礼物。送礼成了定规定制,自然就成了官员们发财的门路,官员贪赃枉法也由此而更盛。
雍正帝对此早已深知,雍正元年即派人对山东省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山东巡抚黄炳每年收规礼多达11万两,其中包括节寿礼,两司茨余(即布政使、按察使交的耗羡银)、钱粮规礼、驿道规礼、粮道规礼等等,可谓名目繁多。而巡抚一年的正项俸银只有130两,禄米130斛,可见他的贪污是非常大的。假如这一陋规不被革除,势必会对当时所推行的改革造成不良影响,所以,雍正帝决定革除这一陋规。
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发出上谕,禁止官吏接受下级官员的馈赠,但由于官员们的俸银普遍比较低,仍是屡禁不止。实行了养廉银制度之后,雍正帝自然有了大力禁止的理由。雍正帝发布上谕:此后绝不允许中央官员对地方、上级官员对下级收受规礼,违者严惩。在雍正帝的指导下,一些得力宠臣也开始致力于破除陋规。
做得最突出的当属河南巡抚石文焯。石文焯在计议耗羡归公时,考虑到如果规礼不除,州县官为应付规礼,还会在耗羡外再行加派以奉献上司,为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石文焯就将巡抚衙门内“所有司道规礼,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田文镜继任后,继续坚持这些规定,他不仅自己点滴不要,手下属员、家人差役等人也绝不许收受些许,如有发觉,即行严治。河南有一些特产,如开封府的绫、缎、绸,归德府的木瓜、枣、牡丹,水田州县的大米,附山州县的木炭、兽皮、兔、鹿等,以前,上司强令该地方官吏交纳,成为定例。田文镜到任后,一概不收,并在全省范围内严厉禁止地方官向上司交纳特产。
陈规陋习一旦形成,就不可能一下子根除。尽管雍正帝下了谕旨,但还是没能彻底根除这种陋习。有的官员希望博得上司的赏识和提拔,仍保留着送礼的习惯;有的上司养成了收礼的习惯,很难适应无人送礼的情状,便暗示下属官员莫失礼效,有礼照收不误。这种情况虽属个别,但肯定是存在的。雍正帝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既然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彻底。凡被参劾、查知收规礼的官员,雍正帝下旨惩罚,轻则罚款,重则罢官、拘禁,给行贿受贿者以沉重打击。
山东省的情况最为严重,尽管雍正帝屡屡下旨,仍有再犯之官。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派升任河东总督的田文镜去严行查禁。田文镜到达山东后雷厉风行地进行清查,对前任巡抚黄炳、蒲台知县朱成元等人的收受陋规案情严行审理,一一参革了他们。此后,官吏们都意识到了雍正帝的做事风格,送礼和收礼的陋习渐渐变少了。
在取缔地方陋规的同时,雍正帝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雍正帝心里很明白,地方陋规与朝中陋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朝中官员要收规礼,地方官员便只好向下面收规礼。因此,要想彻底根除陋规,只有追本溯源,从最高层根除才行。以前,户部在向地方征收钱粮时,每一千两税银中要加派“余平银”(指剩余在银秤上的,其实就是给主管官员的孝敬银子)25两、饭银7两。雍正帝意识到这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源头,因此在继位之初就下令减去“余平银”的十分之一。耗羡归公后,怡亲王允祥建议取消收纳缴银时的“余平银”,并同时杜绝地方官短交(少交)或以“潮银”(即含银量少,成色不足的纹银)抵充足色纹银的行为。雍正帝觉得这个办法能有效地制止朝中官员和地方官员私分国家钱粮的图谋,立即予以批准。
在破除了朝中的加派之风后,雍正帝又把眼光盯在“部费”上。所谓“部费”就是指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果不缴纳一定的礼金,吏部就不予批准实行。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清理亏空的部门,但有一些人也暗中收取这种“部费”。针对这种情况,雍正帝于十二年(1734年)十月谕告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严厉禁止贿赂京官。至此,官场送礼之风才被有效地扼制住。
以上破除陋规的行动,是在实行养廉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官员发财,但他不允许官员损公肥私和额外发财。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肃杀了官场的陈规陋习,整顿了吏治。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这种事情在雍正帝即位前是很突出的。雍正帝很清楚滥设名目、强收杂费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会造成吏治不清。在进行各项改革的同时,雍正帝把严禁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整顿吏治的内容之一,最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又因为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便相伴而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到明代,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百姓怨声载道。即使在收费情况相对较好的康熙王朝,康熙帝也曾直言不讳:地方的“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
乱收杂费现象的制度成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财权与事权不统一。最典型的是明清时期,当时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一方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按时足额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另一方面本应由中央财政包揽的事务却要地方政府负担支出,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税外收费来弥补。二是吏治腐败,官吏的行为无监督制约机制。典型例证是清朝初期一些特权部门以特殊需要为由,提出某些额外加征税费的要求,得到朝廷允许。口子一开,赋外之赋、差外之差、税外之税的现象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成为官员的生财之道。
针对以上两个原因,雍正帝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从而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赋税任务;二是整顿吏治。在这一方面,雍正帝可谓下足了功夫,同时也取得了鲜明的效果。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例如,有车辆出口,需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出门时要验票,一辆小车收银两1.6钱,一辆大车收银两3.2钱,这样一年能收银子1700两左右,这些银两都被府尹、书吏和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出口的猪牛羊按每口0.3钱收费,这一条陋规已经成为定例,没有人敢出来反抗。由于贪官污吏的勒索,商人们为了不做亏本买卖,不得不提高出口货物的物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对这件事早有耳闻,他经过调查后,立即向雍正帝奏报,雍正帝下令严行查禁。最后,释迦保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牛羊出口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违者重罚。雍正帝对他的做法很满意,并给予了一定的奖励。
雍正二年(1724年),有人参奏直隶通州金盏河附近的真武庙和娘娘庙的僧人,对入庙进香的民人竟也“挂号取税”。雍正帝听后十分生气,立即命直隶巡抚李维钧查明处理。经过李维钧的详细调查,这些寺庙虽然没有“挂号取税”之事,但的确有僧人在庙内挂匾通名,为进庙之人料理礼拜事宜,然后收取高额香资酬谢,李维钧当即传令禁止。雍正帝对他的做法颇感满意,夸赞他处理得很及时。
为了彻底根除收费名目,雍正帝在各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例如,江苏省扬州府仪征县,从明朝开始,凡是商人贩运盐引,都要用该县印信钉封,把它作为沿途稽查的凭证。到了清朝,商人在赴县衙钤印时,先按旧例每盐引交银3厘,此为归公引费,另外再加收2厘,为官役饭食费。盐商在县衙交银钤印后,还必须经过驻在仪征专司盐务的掣盐衙门验发盖印。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是勒索,但因为怕拖延时间,耽误运送,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交费。
在查清这件事后,雍正帝认为盐商赴县钤印封引,徒滋纷扰,无益稽查,如果免去这一周折,乱收费现象就会自动取消,商运也可避免阻滞。于是,雍正帝下令盐运归盐政衙门负责,没有必要用该县印信钉封,这就在根本上杜绝了对盐商乱收费的现象。
雍正帝的取缔规礼、严禁乱收杂费制度的出台,是对整顿吏治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清朝的吏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