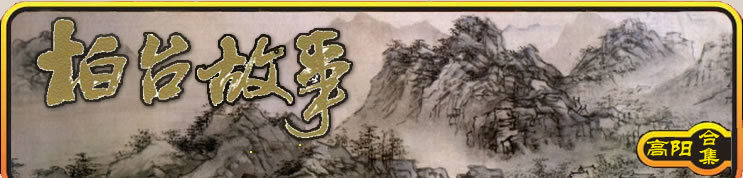 |
|
彭鹏
|
 |
|
|
康熙操纵党争,使令互攻,藉以获知双方的隐私弱点,握有把柄在手,不即发作,只责令其尽心公事。臣下怀德畏威,无不格外巴结。如李光地道学面目早为彭鹏揭破,而康熙任使如故,李光地何得不尽心尽力。至于彭鹏虽一时斥责,亦终究重用,驭下之妙,无与伦比。康熙六十一年盛世,洵非虚致。
许三礼之留任,对徐乾学自是一个警告,因于这年冬天,上疏乞归,自言:
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前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不合经典,臣与九卿从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
愿以“书局自随”,犹冀复起入朝。康熙此时还未决定对徐氏兄弟应持何态度,因而一贯优遇,降旨褒奖。这是二十八年十一月的话,到了二十九年二月动身南归,陛辞时康熙特赐“光焰万丈”匾额。此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嘉美异于常情。但亦可能是警告,改“光”为“气”则“气焰万丈”,便足致祸。
果然,徐乾学回到昆山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便有一奏严劾。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隶镶黄旗,笔帖式出身,居官颇有政绩,谥清端,雍正中入祀贤良祠,凡此恤典,决非幸致,是则劾徐乾学可信其非尽为明珠修私怨。其疏兼劾徐氏兄弟子侄,江苏巡抚洪之杰等,原疏胪列多款,引录如下,以见彼时的吏治绅权:
凡为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负养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如巡抚洪之杰,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谨胪列陈之: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学士,洪之杰谄媚,制金字大匾一方,旗杆二根,旗上金镌“瑞协金瓯,泰开玉烛”八字,委督粮同知姚应凤,赍至徐元文前树立。复送贺仪一万两,徐元文之子,举人徐树本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赵宁,投拜徐元文门下,馈银一千两,徐元文之侄徐树屏、徐树敏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苏松常三府,采买青蓝布解部,以少价买多,支销银一万四千余两,洪之杰、赵宁、徐树本等分肥。
徐元文之子徐树声,自京到巡抚衙门,称有要紧密信,因开门稍迟,喝打门吏,洪之杰听闻,忙即大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道,衙役路人,皆为耻笑。洪之杰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减等案内,部议革职,蒙皇上宽宥降级留任,而元文、乾学冒恩,以为己力。洪之杰将银二万两,令原任松江知府赵宁,送徐树本收。
康熙二十八年,阊门外居民钦涞、钦鼎丞,彼此争讼,徐树敏见钦鼎丞家裕,嘱托巡抚,令钦涞、钦宸枢控告,许钦鼎丞银一千两,交与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兑收。
徐树声兄弟,前往苏州府承天寺内,瞰琅山房恶僧等富厚,诈银一千两,嘱巡抚止留琅山房之僧,余房僧尽皆驱逐。后被逐之僧,及众百姓为留恶僧,反将好僧逐出,公愤怨憾。
徐树本唆王缉植之母,告同县监生李端匏,久不葬亲,诈得李端匏银四百两。
原疏胪列尚多,凿凿有据,但以彼时官场而论,不算大过。因此,康熙从宽处置,只令徐元文休致。但情势外弛内张,而同时及后世对徐氏兄弟颇多怨词,此亦可怪之事,如《清诗纪事》:
元文原品休致,舟至临清,榷关者发视箱箧瓶无遗,冀验其货贿,竟无所得。乾学非能清白自矢者,特狼藉不如人言之甚,身后藏书斥卖殆尽,诸子困穷,非虚饰也。报复者修怨未已,元文、乾学先后以忧死,党局始稍结。元文撰含经堂集三十卷、别集二卷、附录二卷,与乾学澹园集俱无人为之作序矣,盖忧危中虑为人执持,刻成不敢公然行世。
按:今传《园文集》有宋荦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又《十朝诗乘》载:
健庵以尚书里居被逮,门生故旧相率避匿,独韩慕庐宗伯,以小舟送至淮上。秦小岘过昆山诗有云:“平生师友一长洲,患难周旋共白头。”指此。
姜西溟苦寒行谓立斋身后营葬,亲故无视窆者,其诗云:“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狷。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哪得青蝇为吊客。”死生贵贱间,世态如此。
韩慕庐即韩,苏州人,康熙十二年会状。陈寅恪谓江浙间以韩科名得意,所以取名为“”著极多。韩,徐乾学门生,敬礼师门,始终不改。曾有“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
但谓徐乾学“里居被逮”,殊有未谛,被逮者为徐乾学子树敏。《清史稿》本传: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淮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舆珏俱坐是夺职,自是者不已。
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徐乾学之死,据邓石如说:“三十三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死者来,而不测祸幅,遂卒,盖悸死也。”邓石如的话必有根据。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据石蕴玉所撰徐传:“甲戌卒于家,有旨召回己不及矣!”又郑方坤撰徐传:“逾年诏以原官起用,而宣纶之日,即为撤瑟之辰。”皆为隐笔。
邓石如以为徐乾学死后,“文士多作诗哀思之,鲜有刺讥者,不知其何以得此?”此在韩所撰徐乾学的行状中,或可求得解答:
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丧,如检讨陈君维崧、倪君灿、吴君任臣、黄征君虞稷、吴孝廉兆骞,皆公一人为之经纪,不以告人。陆御史陇其有直声,殁而公哭之哀,将为之营葬,且志其墓,会公亡,御史至今葬无时也。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后生之才俊者,延举荐引无虚日……或穷困而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饮助,不足更继之以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僦别院以居之。
登公之门者甚众……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赖公营救得归者,亦比比而然。
按: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顺天乡试副主考,拔韩于落卷中,癸丑联捷为会元,复得大魁天下。韩感于知遇,行状中不免溢美,但大致皆为实情。顺康之际,若钱牧斋、龚芝麓等,爱才好客,一时名士受其惠者极多,徐乾学亦复如此。但此亦为康熙所鼓励,假手于徐乾学笼络名流、安抚士人,当时在江南的曹寅亦负有此种任务。明乎此,可知康熙对“四方玉帛归东海”之谣,淡焉置之,其故安在。更可知徐乾学殁后何以四方文士多作诗哀之,而罕讥刺。
徐乾学“哭之哀”的陆陇其与汤斌齐名,为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是唐朝陆宣公之后,亦为明朝嘉靖年间有名的“锦衣卫大堂”陆炳之后。《清史稿》本传: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景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阙以知县用。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陆陇其入台之时,正当康熙继平三藩以后,策划第二次大征伐,打算亲征噶尔丹。清初用兵,如俗语所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必先遣大员筹办屯积传输之事。户部以军需浩繁,请开捐例,中有一新名目,谓之“捐免保举”。照成例,捐州县保举,须有督抚班子,方得补缺。陆陇其以为保举可以捐免,则捐纳与正途无异,且保举者保举清廉,可由捐而免,则是清廉亦可捐纳而得,因上疏反对,且进一步建议:捐官而三年无保举者,休致。上谕交九卿会议具奏;结果认为三年休致之议太刻,果然如此,求保者奔杂更甚。陆陇其复又上言:
捐纳一途,实系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虽不敢谓督抚之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贪污之辈,自有督抚纠劾,而其侥幸获免者,遂与正途一体升转。虽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辈无不先期捐纳,即无不一体升转未可云无碍也。至于到任三年,无保举者令休致,谓恐近于刻,不知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俨然列于缙绅,为荣多矣。若谓将届三年,辄营求保举,此在督抚不贤,则诚有之,若督抚贤,何处营求?且即使督抚不贤,亦必不能尽捐纳之员而保举之,此休致之议亦从吏治民生起见。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
其时捐免保举者极多,因陆陇其一疏,事在未定,以致多持观望。户部大为不满,策动九卿,作成一项决议,以陆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捐生“犹豫观望,紧要军需,因此延误”,奏请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
所谓“发往奉天安插”,即是编入汉军,成为旗人。这是当时对有民族意识的汉人,最恶毒的精神侮辱。幸而圣祖之为圣,知道陆陇其极得民心,畿辅百姓,多以陆会充军担心,因而降旨宽免。不久,复命巡视北城。巡城御史犹如地方官,北城又为内务府及太监聚居之处,想来陆陇其必有一番裁抑豪强的举措,可惜史无可征。
陆陇其和平笃厚,涵养功深。《三鱼堂日记》有一条云:
辛未六月十四日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划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
后人就此条日记,评论陆陇其的为人,颇为公允,其言如此:
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一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言,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哪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三鱼堂”为陆陇其的祖父所筑,得名由来有一段故事,《清朝野史大观》记: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且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圣德之,溥子束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堂,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
他书亦有此记载,所督运者为公款,倘或出事,责任不轻。三鱼塞漏,嘉其不欺。汤、陆之为真理学,即以表里一致,而言行亦自有曲体人情、循枉求直之处。《清人笔记》中记其轶事,可见其人:
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入或咎公失言,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公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迳出,学士知,亟疑留之,而棹已返矣。
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此皆深得孔子拜阳货之教者。汤陆之可敬,即在不腐不迂、不托空言,讲求事功,内心极方正,但手段出以圆通。汤陆讲理学,皆深恶袖手谈心性,但陆遵程陆之微逊于汤者,以某观之在此。
陆陇其殁于康熙三十一年,正徐乾学受佛伦所攻之时。康熙曾欲用陆为江南学政,闻其巳卒,乃用与陆同时行取为御史的邵嗣尧。死后授官,不过陆陇其的哀荣之一,生平定价,犹在数十年以后。《清史列传》本传:
雍正二年,临雍释奠,论九卿议增文庙从祀贤儒,因议曰:“陇其自幼以斯道为己任,精研程朱之学,两任邑令,务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实能发前人所未发,弗诡于正,允称纯儒,宜配享俎豆。”得旨俞允。今上乾隆元年,诏九卿核议,应予追谥诸臣,因议曰:“宋儒胡瑗、吕祖谦诸儒,皆未居显职而有谥。陇其虽官止五品,已从祀文庙,应予追谥。”上特赐谥曰“清献”。
寻礼部以会典未载五品官予谥立碑给价之例,请上裁定。得旨:“陆陇其着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照例给予碑价。”
同时赐谥者有汤斌。汤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官工部尚书,但为降七级留任。殁后虽得旨照尚书例祭葬,却未予谥。乾隆元年,特谥“文正”。清朝得谥文正者共八人,除曾国藩以事功差可企及外,其他视汤斌皆不能不深惭。彭鹏附记:李光地
汤陆皆为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这一榜得人甚盛,但同年之间,恩怨纠纷甚多,充分反映了康熙初期仕途上的复杂。徐乾学以外,李光地的是非亦很多,与陈梦雷的纠纷亘数十年无定论,直至傅增湘印《榕村语录》,方知李光地与陈梦雷合作投机,李光地确有“卖友”之实。
此外“夺情”及“外妇之子”,合而为李光地三惭德,尤以“夺情”一事,将李光地的假道学面孔,剥露无遗。发难者莆田彭鹏为有名的一桩柏台故事。彭鹏其人,我以前亦曾说过,但语焉不详,于此愿作一比较完整的介绍。
《清史稿》本传: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
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自其宽。
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
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按:耿精忠在福建作乱,命官缙绅被迫受伪命者甚多。彭鹏坚卧不出,达三年之久。乱定后,撰有《千日大梦记》。李光地家居上游安溪,本可自免,但竟至福州观望风色。赖陈梦雷力劝,始定合作投机之谋,即由陈梦雷受伪命,而由李光地输诚朝廷。如果耿精忠事成,陈梦雷自不愁富贵;耿精忠失败,则由李光地出面证明陈梦雷“身在曹营心在汉”,即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中所谓“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
后来李光地的“节”倒是“显”了,却未“述”其“功”,甚至有落井下石的行径。此即“安溪卖友”的真相。彭鹏必深知内幕,心薄其人,因借“夺情”一事,褫其假道学面目。
彭鹏初授三河知县。此地旗汉杂处,有名难治,又多盗,平剧中的窦尔墩,实有其人,《清稗类钞》记:
窦开山,乳名尔墩,一曰二东。兄大东,皆献县剧盗,能舞枪。使人对面放镖,十镖齐发,尔墩能枪锋抵镖锋,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双刀,尤压倒侪辈。尝劫一巨室,官捕之急,侦得其所在,往迹之。尔墩持双刀闪舞而前,捕卒未见其人,但若有白练一尺,旋行而过。遥望之,隐隐然犹在目,不知其已远数十里外矣。
捕卒等视所骑马二十五匹,其尾尖俱截去尺许,始恍然叹其艺之精,非所敌也。
彭鹏因“缉盗不获,累被议”,即因缉捕窦尔墩,不能得手。但窦亦为之敛迹,民间仍受彭鹏之惠。相传康熙巡视近畿时,彭鹏有调动的消息,三河县民叩辇陈情,欲留彭鹏。康熙表示:“另外给你们一个好官。”有少女抗声而答:“把那个好官给别处地方好了。”康熙为之冁然。升平盛世,君圣官贤,乃有此佳话,不能不令人向往。
彭鹏于康熙二十九年行取为御史,劾李光地“贪位忌亲”,事在三十三年。《清史稿》本传:
三十三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
按:李光地自康熙十九年八月至京,由编修超擢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即因陈梦雷的讦告,徐乾学等人的杯葛,不安于位。二十一年五月乞假送母归里。至二十五年七月始再赴京,授翰林院掌院。
翌年三月,复又乞假归省,至二十七年四月,奔孝庄太后之丧回京,犹为礼部以“在途迁延”所劾。一官如寄,来去不定,可知处境极苦。及至三十三年正月,放顺天学政,四月即丁忧,得旨:“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着在任守制。”
父母之丧三年,是名教中最看重的事。康熙此旨,实在是要试一试李光地究竟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真道学则必奏请解任,回籍守制,甚至拜折即行,不问允准与否,亦不算忤旨。
哪知李光地因为自复起后,居官之日少,在里之日多。如今再回乡守制三年,与朝廷脱节,将来服阕回京,人事全非,再想如现时之帝眷之隆,将不可得。因而上疏乞假九月,回里治丧。这一来滋人口实,群起而攻,《清史列传》本传:
光地疏言:“苦块余生,重荷圣恩之厚,圣知之深,敢不以残喘自效?顾虫蚁微情,乞给假治丧,住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岁科两试,可以看阅周详,报竣无误。”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诚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绛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属在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颜充位?
当日奉旨,仍如初命。于是彭鹏发难,一开头就说:“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接下来说李光地有“可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可留者无非“报亲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此已讥其功名之念重于报亲之心。不可留者十,前面五条,与沈恺曾、杨敬儒所言,大致相同。后面五条,咄咄逼人,词锋极利:
六、光地疏称荷圣知之深,残喘自效,请假九个月,不误学差。佥谓九月大功服,谈言微刺。
七、定例生童匿丧应试,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起而诘曰:“侍郎何至此?”光地何辞以对?
八、学校所以致天下之为臣思忠,为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伦”。光地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
九、本年正月,皇上面议诸臣于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三申意焉。试问光地今日礼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
十、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谊何敢辞?”臣闻宋臣富弼母丧,王起之固辞,且日:“起复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许之,纲目大书,以垂训后世。又宋孝宗起复刘琪,六疏固辞,发明曰:“纲目书固辞予之也。”我皇上尧舜比隆,教孝教忠,必无有辞之而弗允者矣。
康熙得奏,一面将原疏交九卿会议,一面传旨询问彭鹏。据李光地之子《钟伦家书》,旨问:
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何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
所谓“自有深意”,即言欲借此以试李光地。所谓“包容”,即言不说破已试出李光地为假道学。最后两句话,是以为彭鹏欲为李光地补救,仍旧得以回籍服三年之丧,稍得保全道学面目。彭鹏因而有第二疏。古今诛心之论,未有深刻若此者。兹分段录引如下: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然镜照而无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憨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
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血,谁甘面从?
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家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
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
此奏一上,竟如所请,命“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一个多月以后,康熙召试翰林官,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自然是因此事而发。康熙有意试李光地的人品,亦获得证实。而李光地之狼狈,可于其子李钟伦家书中见之:
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楚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
李光地在京守制,服满起复,仍授顺天学政。彭鹏亦外放为贵州臬司,升广西巡抚,调广东,四十三年正月殁于任上。在康熙四十年左右,圣祖以为督抚中最清廉干练的,共得四人:湖广总督郭、河道总督张鹏翮、直隶巡抚李光地、广东巡抚彭鹏,每举以并称。除彭鹏外,另三人皆康熙九年庚戌两榜出身,李光地二甲二名,张鹏翮与郭皆在三甲,名次几相连,一为一百二十二,一为一百二十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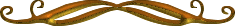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