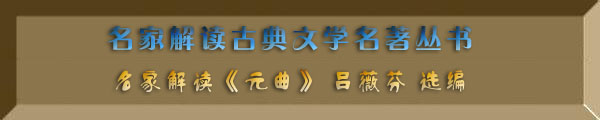黄天骥:独具特色的散曲呈文
|
|
——谈刘时中的《上高监司》
刘时中的《上高监司》,是元散曲中最长的套数,是作者似散曲形 式向高监司献呈的两通说帖。
元代散曲作家有两个刘时中,一是石州宁乡(今山西平阳)人,曾 任翰林待制等职。另一个是洪都(今江西南昌)人。在此散曲中,有“据 江西剧郡洪都”一语,写江西发生的事情,可知此曲作者,应是江西的 刘时中。
元刊《阳春白雪》收有署名为刘时中的[新水令]《代马诉冤》,以 马的口吻诉说“世无伯乐”,“把我埋没在蓬蒿,失陷污泥”。情绪十 分悲愤。山西的刘时中,世代簪缨,高官厚禄,不可能有这样的情感, 它只能是江西刘时中的作品。由此也可推知,这一位刘时中是胸怀大志 而又穷愁潦倒的人物。
高监司是谁?现在已无法得到确证。较多学者认为司能是天历初 (1328)任河西道访廉使的高纳麟。《新元史》卷一百五十六《高纳麟传》 载:“天历元年(1328)除杭州路总管,明年改江西道廉访使。岁饥,议 发粟赈民,行省难之。纳麟曰:‘朝廷如不允,我愿以家资偿之。’议 始决。全活无算。又劾罢贪吏平章政事八失忽都,民尤颂之。至顺元年 (1330)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上高监司》写到江西人民遭受旱灾, 歌颂监司开仓济民;写到钞法弊病丛生,建议监司惩治猾吏。这些和元 史提到高纳麟在江西南昌的政绩颇似。曲中还写有“已自六十秋楮币行, 则这两三年法度沮”两句。据查悉,元代发行楮币始于中统元年(1260), 距天历元年有六十多年。如果“六十秋”是约数,那么,从作品所写的 情况看,与高纳麟的事迹颇多吻合之处。《上高监司》的第一首又有“一 座祠堂人供养,立一统碑碣字数行,将德政因由都载上,使万万代官民 见字节想”等句子,极似是为欢送高监司离任迁升而发。史载高纳麟于 天历元年莅任,于至顺元年离赣,那么,这套曲子,当是作于 1328 年与1330 年之间。
1329 年,“江西隆兴、南康、抚瑞、袁、吉诸路旱。”《上高监司》 的第一首,写的就是江西干旱荒芜的景象。在曲子开头,作者说:“谢 恩光拯济皆无恙,编做本词儿唱。”高纳麟曾经赈济饥民,刘时中以曲 代书,本意是要歌颂他的德政的。但要具体写到高监司拯厄扶危,就不 可能不如实地反映江西的现实,这一来,作者以淋漓的笔墨,向读者揭 示元代人民悲惨的生活面貌。
在第一曲[滚绣球]里,刘时中对当时旱象作了简练的概括:“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时取若时雨降,旱魃生四野灾伤。”插秧时节没 有雨水,秧插不下去,“谷不登,麦不长”,结果“万民失望”。并且 导致经济混乱,“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 煞是凄凉。”这首曲,纯粹是叙述性的,作者由无雨说到缺粮,由缺粮 说到灾荒,特别强调物价高涨引起的严重后果。曲子的形象性不强,但 叙述的脉络清晰明确,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刘时中对饥民痛苦的生活,作了细致的刻画。当时米珠薪桂,人民 只好以野菜充饥。作者写道:“剥榆树飧,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 掌,蕨根粉以代糇粮,鹅肠苦菜连根煮,获笋芦莴带叶■,则留下杞柳 株樟。”黄不老、鹅肠苦菜、荻笋、芦莴都是不能下咽的东西,但饥肠 辘辘的人,把它们看成是胜如熊掌的山珍海味,把它们“连根煮”,“带 叶■”,饥不择食,狼吞虎咽。更有甚者,“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 是煮麦麸稀和细糠”。饥民们如果有了点和糠米豆菽凑合的杂粮,就简 直像得到了神仙的赏赐,“他每(们)早合掌擎拳谢上苍”。饥民们“一 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在街巷里横七竖八,卧而待毙。为 了求生,有些饥民,铤而走险,“偷宰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 有些始而贱卖家业,继而卖儿卖女,卖不去的哺乳小孩,“没人要撇入长江”。这一幕幕哀鸿遍野、惨绝人寰的景象,作者以饱蘸血泪的笔触 一一勾出,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元代的社会现实。
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有些人却大发横财。刘时中敏锐地看到,投 机商贩,倒卖粮食,操纵市场。他们趁火打劫,“牙钱加倍解,卖面处 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而有权有势的人,则巧夺豪取,把义仓 米粮据为己有。所谓开仓赈米,只“快活了些社长知房”,他们可以“用 钱买放”仓米,囤积居奇,肆意盘剥。面对着不合理的现实,刘时中愤 怒地控诉剥削者吮髓吸膏的现状:“殷实户欺心不良,停塌户瞒天不当, 吞象心肠歹伎俩,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怎指望他儿孙久长。”这 番话,一掴一个血痕,充分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在元散曲中,有些作品也写到人民的生活,但很少像《上高监司》 写得那样锐利深刻。刘时中要叙述江西的旱灾,但没有用多少笔墨描写 旱象,没有渲染烈日蒸云,赤地千里,倒是抓住缺水导致缺粮这一点, 铺写“殷实户”、“停塌户”以及“社长知房”的乘“饥”搜刮。作者 还有意把饥民和富户在旱灾中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
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 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显然,作者要让人们看到,江西人民的灾难,天灾只是诱因,根源在于人祸。正是人对人的剥削,造成了饿殍“填街卧巷”、小民“鬻妻卖子”的惨剧。当然,刘时中过分讴歌“秉心仁恕”的高监司,把“恤 老怜贫”、“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但是,他透过 现象,看到本质,质朴而又酣畅地揭露社会的不平,这实在难能可贵。 在元代后期,许多散曲作者越来越脱离现实,或是徜徉山水,或是沉湎 酒色,所写的作品,多数内容贫乏、调子委靡。刘时中却直接描写人民 的生活,尖锐地揭露社会弊端,显得有血有肉,热气蒸腾。这套曲之所 以值得重视,绝非因为它是散曲中最长的一首,而是因为它写得鞭辟入 里,具有较高思想价值。
《上高监司》第二首,则以揭露元代钞法积弊为主题。作者指出,
当时一些“买卖人”和官吏勾结。“这一个图小倒,那一个荀俸禄,把 官钱视同己物”;有些人从中舞弊,发了大财,“一家家倾银注玉多豪 富,一个个烹羊挟妓夸风度”,“受用尽人间福”。作者认为,钞法是 “黎民命脉”,积弊不除,便会“坏尽今时务”。他痛骂那些钞法的破 坏者,说他们是“向库中钻刺真强盗”,建议高监司对扰乱金融的人严 刑峻法,认为“法则有准使民服,期于无刑佐皇图”。作者不可能知道, 钞法的混乱是封建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但他的散曲具有帮助人们认识 元代社会的价值。《上高监司》两套曲,揭露社会的重点虽有不同,而 作者认为人祸是罪恶的渊薮,这一思想,却始终贯串在两曲之中。刘时 中看到封建社会有一层人胡作非为,看到吏治的腐败,这在客观上使读 者看到了元代社会腐烂的躯体,看到“奸蠹”们如何吮吸人民的膏血。
《上高监司》语言朴实无华,作者以赋的手法,铺陈己见。刘熙载 说:“词如诗,曲如赋,赋可以补诗不足者也。”(《艺概·词曲概》) 这段话,主要是说词与曲的关系,但也指出曲具有赋的艺术特点。赋, 就是铺陈。由于曲可以大量加插衬字,有利于作家连贯地联结意象,酣 畅地直抒胸臆,而不像诗或词那样形象跳跃,要借助读者的想象领会意旨。尤其曲的套数,“可以任我铺排。”(同上)不过,我国文坛经常 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立的文体互相转化。例如,散文会向 韵文转化,成为骈文;凝炼的诗也会向散文转化,成为类似散文的诗。 散曲的特点,本在于“散”,初期散曲作家正是以其俚俗流畅铺陈透彻 的写法饮誉文坛,而与南宋词坛工巧典雅的格调鲜明对立。不过,到元 后期,散曲却词化了。许多散曲作者追求婉丽蕴藉,作品写得像挂着曲 牌的词。请看张可久的《湖上》:“二客同游过虎溪,一径无尘穿翠微; 寸心流水知,小窗明月归。”如果抽掉[越调·凭栏人]的曲牌,它与词 又有什么两样?真是“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在曲向词 转化,被吹回到词的老路的时候,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却以大量生活 口语入曲;铺陈跳挞,议论透辟,以说贴体写曲。既坚持散曲俚与散的 格调,在形式上又有所创新,这些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选自黄天骥:《深浅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